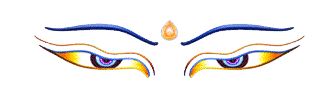论藏传佛教前弘期
班班多杰
佛教传入前吐蕃社会的政治经济背景
佛教是公元七世纪初正式传播到吐蕃地区的。为什么这个时候被藏民族所接受呢?简单地说,它适应了当时吐蕃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也就是说,佛教思想是在藏族社会摆脱传统社会结构与意识形态,由分散的部落,逐渐成为统一的封建帝国的历史条件下传播和发展起来的。
吐蕃社会发展到松赞干布的祖父达日宁赛时代,就已经是相当兴盛了,在政治上开疆拓土,疆域“北至雅鲁藏布江,与苏毗为界;东抵康,与四川北部的嘉良夷为界,以附国之名为隋朝的统治者所知;西部达到羊卓雍湖,与西部的三鲁雅下部为界;南面邻接尼泊尔和不丹,已包括青藏高原南部的主要部分。(1)据藏文史书《贤者喜宴》记载:“将当时三分之二的小邦均纳入(吐蕃)统治之下。巴本王、吐谷浑王、昌格王、森巴王及香雄王等均被征服,娘、贝、嫩等氏族也被纳为属民。(2)由此可知,当时吐蕃的努力范围有了明显的扩大。
从经济上看,已经出现了统一的度量衡。据藏文史书记载:“这时墀托朗尊蒙之子制造升、斗和秤,以量谷物及酥油。在此之前,吐蕃尚无交易及升、斗和秤。”(3)这说明当时吐蕃的经济发达。此时还有“杂交出犏牛与骡、确定物价、储存干燥之山草(4)等习惯。说明当时吐蕃地区的农、牧、商业已有了很大的发展。
达日宁赛的儿子便是雅隆部落中有名的赞普——朗日松赞,他为统一青藏高原,发展农牧业生产,增强吐蕃势力,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从经济上看,当时在冶炼技术、驯养和改良牲畜、取用食盐、采用医药、制造武器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发展。据《松赞干布遗训》载,这时的吐蕃人,“将公母野牦牛驯养为公母牦牛,将公母鹿育成黄牛,将公母山羊驯养为绵羊,将公母獐驯化成山羊,将公母野驴驯化成马,将公母狼驯化成犬。”进一步开发了金、银、铜、铁等主要矿产。据《松赞干布遗训》一书中载:“朗日松赞建强农米久宫堡,于蔡崩山得金,于格日岩得银,于城波崖得铜,于热嘎山得铁,于北方拉措湖得盐。”这说明朗日松赞时期的采矿业很发达。军事技术也得到了相当大的发展,《贤者喜宴》记载:“征服边地之佳及突厥。于新年之际,将绵羊的生肉腿堆积起来,然后攀其上,佳地之城堡遂被攻陷;又用藤子制成引火物,将其系在铁钩中腰,随后抛出,此即谓‘火烧佳地’”。这不但说明吐蕃在攻城技术方面有了新的成就,而且还说明他们已学会了一些火攻武器的制造。
社会经济的发展,为雅隆部落的北伐打下了物质基础。《敦煌吐蕃古藏文文选》中记载:当朗日松赞攻下宇那堡,苏毗王芒波杰孙波逃往突厥,并将岩波地方改为彭域(5)。此时朗日松赞的势力西到香雄,《拉达克王统记》一书说:朗日松赞时“征服天竺、突厥及西方尼雅秀等诸王。”(6)此即《贤者喜宴》一书中说的十二小邦中的香雄王黎那许;东达工布、娘波及温地;南至达波、雅隆、门;北抵彭域及羌塘拉措湖,甚至接近西北的突厥。朗日松赞在征服江北拉萨河流域及彭域一带苏毗之后,属民赞他“政高于天,位固于山,乃上尊号为朗日松赞”(7)。朗日松赞为了嘉奖有功之臣,即给各地方首领分封了奴隶和土地。据《白史》记载:“朗日松赞分赏有功,将萨岗辛地方、墨竹地方的1500户奴隶,赏赐跋伊曹,将宇杰松之补布城堡及1500奴户,赏赐娘僧古,将温地方之门喀农民300户,赏赐切波那森,将科那之侬家兄弟1500户,赏赐侬波,并将娘、跋、侬、切波四人任命为赞普之臣,赐与许多奴户和广大土地。”(8)
以上这些情况都说明,朗日松赞之时,由于悉补野的势力范围的扩大,使大部分卫、藏地区基本上纳入了其管辖的范围。但是新形成的吐蕃悉补野政权并不巩固,统治阶级内部发生了尖锐的斗争,出现了父王被杀、属部叛乱的动荡局面。据藏史载:“赞普松赞干布时,父之属民逆行,母之属民反叛,亲戚香雄、牦牛(部)、苏毗、尼雅尼达布、工布以及娘布皆叛。父王朗日松赞被进毒而逝。”(9)这样,刚刚形成的统一政权又遭到了严重的分裂,形势岌岌可危。
公元7世纪初期,吐蕃地方出现了民族英雄松赞干布,他13岁时其父朗日松赞死去,“王子松赞幼年亲政,先对进毒为首者断然尽行斩灭,令其绝嗣。之后,叛者之庶民复归治下。”(10)这是说,松赞干布继承王位后,首先内惩奸臣异己,外讨叛乱属部,斩绝了毒死父王的叛臣及其世系,平息了贵族勾结属部地方势力发动的战乱。迁都拉萨,以拉萨为都,用武力使东女和白狗、哥邻、逋租、南水、弱水、悉董、清远、咄霸等西山诸羌臣服吐蕃,苏毗、羊同、党项、吐谷浑亦先后为吐蕃所并,从而完成了统一吐蕃全境的大业(11)。为巩固统一,松赞干布建立了具有吐蕃本地特色的管理体制,将吐蕃划作五大“茹”,划定十八个地区势力范围,划分六十一个桂东岱的军事行政组织,组成了从上到下的军政管理机构(12)。还设立了三尚一论、内相外相等官职,协助赞普管理全藏的政治、经济、法律等事宜。例如当时以大相吐米桑布扎等“四贤臣”辅佐赞普,对吐蕃王朝的建立和巩固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松赞干布采取了一系列具有吐蕃本民族特色的施政措施和法令,制定了六项原则、六种告身、六种标志、六种褒贬、六种勇饰、六部法典(合称吐蕃三十六制)(13),起到了维护政权、发展经济的作用。
松赞干布还明确划分了属民中的各阶级,例如划分为“桂”、“庸”、“更杨”等(14),以便根据不同的阶级、社会地位分而治之。
总而言之,当时的吐蕃社会有了自己一整套军政体制、职官制度、法律条文、阶级等级。政权的巩固、政治的稳定促进了经济的繁荣发展。
吐蕃的农业,大部分在藏南河谷地区,农作物以青稞、小麦、豆类为主。松赞干布时,“地高蓄水为池,低地于河中引水灌溉……开辟阡陌。”并用牦牛、马作为耕田的工具。“阡陌之制”大约是指封建领主庄园制度的建立。
在牧业方面,“开拓荒地,划分良田牧场”,春夏季逐水草而居,秋冬季有固定的牧场,呈现了一派“牛羊繁殖,沿路成群”的兴旺景象。
商业贸易也有了较大的发展。公元7世纪始,吐蕃与东北的汉地、突厥、西域东部,西北的拉达克、于阗、龟兹、喀什、克什米尔和印度的西部,南部的尼泊尔、四川等地建立了广泛的贸易关系,用本地的麝香、绵羊、牦牛尾巴、毛料、马、宝石、药材、工艺品等换取别国的丝绸、纸墨、茶叶、宝剑等,既繁荣了经济,又吸收了别国的先进文化、技艺(15)。
在工业方面,吐蕃有冶炼、石凿等工匠,尤其在冶炼方面不仅能造刀剑,还能架起铁索桥,冶炼技术已达到较高水平。
公元七世纪的时候,吐蕃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方面之所以取得如此重大的成就,就是因为以松赞干布为首的吐蕃王朝实行了对外开放政策,广泛地吸收和采纳了周边诸多国家、地区和民族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成果。藏史名著《贤者喜宴》详细记载了这一史实:“自东方汉地及木雅,引进了工艺及历算之书;从南方白色的印度翻译了诸种佛典;由西方之胡部泥婆罗,掘开了享用食物财宝之库藏;于北方霍尔与回纥获得了法律及事业之范例。如是,松赞干布遂统治四方,并将一切享用的文明财富(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聚敛在自己所统辖的范
围之内。”(16)这就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道理。古今中外的文明史说明,一个民族、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文明成果,一是靠自己的认识和创造,其次便是从其它国家和民族中借鉴、吸纳和引进,并且将他人和自己的文明成果融会贯通起来,变成自己的东西,才能进入先进民族和国家的行列,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反之,一个妄自尊大、闭关自守、墨守陈规、坐井观天的民族,则只能是落后、贫穷、软弱、愚昧、挨打。松赞干布以他博大的胸怀,广阔的视野,开放的心态,博采众长,兼收并蓄,把邻近先进国家和民族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接纳过来,为我所用,这也是当时吐蕃王朝威震四方、称雄东亚的原因之一。
松赞干布传播佛教
学术界一般认为,佛教正式传入西藏地区是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王执政的吐蕃王朝时期。还有一种说法是,佛教是在松赞干布王的前五代赞普拉脱脱日年赞在位时,由天而降传入吐蕃的。藏史记载,自天空降落《宝箧经》、《百拜忏悔经》、《六字大明咒》以及金塔等等,对此,拉脱脱日年赞王等既感到惊奇和神秘,又认为是珍宝,但不知是何物,于是给它们取名为“年波桑哇”,即玄秘神物,放置在宝座上加以供奉,没有传播开来。我们认为,即便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实质上也谈不上佛教在吐蕃的传播。因为当时的人们还不懂得这些佛教典籍为何物,只是作为秘密而重要的东西供奉着,并未发生过实际影响和作用。客观地说,松赞干布建立吐蕃王朝时,佛教才从印度和汉地正式传入西藏。松赞干布对佛教在西藏地区的初步传播起了如下作用:
松赞干布通过尺尊、文成二王妃把大量的佛经、佛像、法器等从尼泊尔、汉地带到了雪域高原——吐蕃。在两位公主的倡导下,有一些印度、尼泊尔、汉地的僧人进入西藏传法,这些都为佛教在西藏的传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此时佛教的主要活动是建立道场和翻译经典。为了使佛教在西藏立住脚,在松赞干布的大力扶持下,尼泊尔尺尊公主修建了大昭寺,汉地文成公主建筑了热摩伽寺(小昭寺),松赞干布建了迦刹寺等共十二寺于拉萨四周各地。各寺所供的佛像很多,例如释迦、弥勒、观音、度母、佛母、马头金刚、甘露明王等。此外,又建筑了很多修定的道场。
当时已开始翻译佛教经典,“有印度的阿 黎古萨惹,婆罗门香嘎惹,尼泊尔的阿 黎西那曼珠,汉地的阿 黎哈香玛哈德哇泽(意为大寿和尚),以及译师吐米桑布扎及其助手达摩阁侠和拉隆多杰等人翻译了各种经典,并作了审定。”(17)译出的经典有:《宝云经》、《观音六字明》、《门曼德迦法》、《摩诃哥罗法》、《吉祥天女》、《集宝顶经》、《宝箧经》、《观音经续》、《百拜经》、
《白莲华经》、《月灯经》,有说亦曾翻译了《十万颂般若经》(18)。
通过以上几个渠道,佛教开始在吐蕃传播起来了,但只是在王室宫廷的狭小天地内获得信奉,到赤松德赞时才逐渐普及于民间。
松赞干布对传播佛教所起的主要作用是为佛教在西藏的独立发展指出了方向。文化交流史证明,一种外来的异质文化要想在一种新的环境中传播和发展,主要就看它能否与当时当地的政治、经济状况相结合、相适应。松赞干布的机智就在于当佛教的种子一播到高原的土壤中,就为我所用,效法佛教的戒律,结合吐蕃的实际情况,制定了吐蕃的法律规范及道德规范。
西藏在吐蕃王朝以前没有系统的法律制度,对臣民的善恶行为没有完整的赏罚标准。松赞干布建立了统一的吐蕃王朝以后,深感以法治国的重要性。据《贤者喜宴》载:“如无法律,则罪恶蜂起,我之子孙及尚论等人将沦于苦难,故当制法。”(19)于是便命令吐米桑布扎制定法律,“吐米等率领一百大臣居中理事,尊王之命,仿照(佛教)十善法的意义在吉雪学玛地方制立吐蕃法律二十部。”(20)即:
1杀人者偿命,斗争者罚金;
2偷盗者除追还原物外,加罚8倍;
3奸淫者断肢,并流放异地;
4谎言者割舌或发誓;
5要虔信佛、法、僧三宝;
6要孝顺父母,报父母恩;
7要尊敬高德,不与贤俊善良人及贵族斗争;
8敦睦亲族,敬事长上;
9要帮助邻居;
10要出言忠信;
11要作事谨慎,未受委托,不应干涉;
12要行笃厚,信因果,忍耐痛苦,顺应不幸;
13要钱财知足,使用食物与货物务期适当;
14要如约还债;
15要酬德报恩;
16要斗秤公平,不用伪度量衡;
17要不生嫉妒,与众和谐;
18要不听妇言,自有主张;
19要审慎言语,说话温雅,讲究技巧;
20要处世正直,是非难判断时,对神立誓(21)。
在这二十条法律条文中,前四条是根据佛教的五戒制定的行为规范,叫作“戒恶”,后十六条也是根据佛教十善的精神制定的,作为人民遵守的道德行为规范,叫作“劝善”。
把佛教“五戒”、“十善”作为立法依据和道德标准,根据吐蕃社会的实际情况制定的这些法律和道德规范,在吐蕃广大臣民中起到了“对善人予以奖励,对恶人加以惩处,对豪强大族用法律压抑,对贫弱者设法扶助”(22)的良好作用,更重要的是从此以后在藏民族的心理中逐渐树立了一种“出世”、“解脱”的理想境界,并且形成了一种为之而奋斗的行为准则,即慈悲、行善、知足、正义、宽容、自谦、诚实、和谐、义务、贡献等,这种外在的规范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
逐渐变成了藏民族内在的文化心理特质。为什么会产生如此效果呢?这是因为以松赞干布为首的吐蕃王臣们把印度佛教的某些戒律藏族化了。对这种藏族化,我们不能理解为对传统佛教思想的扭曲,而是藏族人根据当时吐蕃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的需要,对异域文化的一种蒸馏。而这样的蒸馏是两种文化交融汇合必不可少的过程,只有这样的过程,异质文化才能进入自己的文化圈而发挥作用。
赤松德赞发展佛教
印度佛教在赤德祖赞以后的广泛传播,引起了西藏传统思想文化苯教与外来思想文化佛教的矛盾和冲突。正是这种矛盾冲突,推进了佛教思想文化的发展。
印度佛教传入吐蕃时,传统思想苯教就对其怀有敌意,有时也产生一些小小的对抗。如当大小昭寺“建造到108座神殿时,夜晚即神鬼彻底摧毁”。这些民间传说虽近于梦幻,在一定程度上确也反映了佛教和苯教的早期对抗。然这个时期佛苯之间尚未掀起比较大的干戈,待到二教之间接触稍深后,实质性的不同逐渐发现,冲突便随之而起了。
佛教和苯教的实质性斗争是在赤德祖赞王死后开始的。赤德祖赞王去世时,赤松德赞王年幼,握有实权、左右朝政的大臣玛祥·仲巴杰等大贵族势力制造种种借口来反佛崇苯。仲巴杰说:“王之短寿乃系推行佛法之故,遂不吉祥。所谓后世可获转生,此乃妄语。消除此时之灾,当以苯教行之。”(23)并采取了一系列灭佛措施:
1“将崇佛大臣朗与贝二人定罪,发往吐蕃黑暗(之地)。”(24)
2“将小昭寺之金释迦牟尼像……埋在沙沟之中。”(25)
3“一位担任香灯师的汉地老和尚,也被驱回汉地。”(26)
4“卡查神殿被彻底推翻,(查玛)珍桑神殿被毁,其间之钟被送到秦浦之岩石处。”(27)
5“将逻些毕哈尔神殿处当做作坊,屠宰牲畜之后,即将牲畜之皮盖于泥塑神像之上,神像手中托着牲畜内脏及羊的腔体。”(28)
不仅如此,他们还决定,今后“谁推行佛法,便将其孤身流放边地。并制定了不准推行佛教之小法律。”(29)总之,当时吐蕃社会处在老王已死、幼主无权、苯教盛行、贵族当政、王室受压、佛教被禁的状态,桑希等人到汉地学佛取经回藏后,因迫于这种形势,不得不“将各种汉地(带来的)佛典埋藏于秦浦的荒山缝隙之中”,把请来的汉僧又送回了汉地。
赤松德赞成年亲政后,读到先前诸文书,便知道前代诸王笃信佛教,曾大力弘扬佛法,于是引起了对佛教的信仰,并与桑希、贾桑梅果等众臣讨论复兴佛法的事宜。至此桑希认为弘法时机已到,遂“将藏在秦浦岩中的佛典取回”,上呈藏王赤松德赞,并首先给藏王“诵读了《十善经》,对此,赞普生起信仰之心,领悟了善行;继之,又诵读了《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于是(赞普)又领会了正确见解,从而生起大信心;复诵《佛说稻竿经》,(赞普)因之了解了双修,由是笃信佛法。又有的说:(桑希)先在赞普面前极精炼地讲述了十善和五蕴,随后又传布了《佛说稻竿经》,因此(赞普)乃从一切佛法之因缘中生起信仰之心念”,进一步了解了佛教的具体内容,认识到了弘扬佛法的重要性,说:“如此之完好的佛法,在我之时获得,当酬谢天地菩萨等一切神佛。”并颁布敕喻道:“我先祖行佛,而玛祥毁之,此事甚恶。由于舅氏尼雅桑又言,遂乃复迎汉地之神像,我等仍宜奉行佛法。”并采取了一系列兴佛措施。
1派人到长安取佛经、请汉僧。
2颁布奉行佛法的诏令。
3将先前被苯教徒驱除的释迦牟尼佛像从芒宇地方请回了拉萨,仍供在大昭寺正殿中。
4命令桑希等把他“所迎来的全部汉地佛法、藏域的诸佛典等,与汉人梅果、印度阿年达及精通汉语者加以翻译,此三人在海波山的鸟穴内将佛典译成藏语。”
5与崇佛大臣一起定计翦除了反对佛教的大臣玛祥·仲巴杰等人。
6派人到尼泊尔迎请著名佛学大师静命。
从赤松德赞的这些行动中即可看到,他在消除了统治集团内部以玛祥为代表的反佛势力之后,便在信佛大臣的支持下积极寻求佛教,欲图以此作为巩固政权的精神武器。
佛教与苯教之间第二次斗争是在静命论师到藏后开始的。通过第一次佛苯斗争,虽然佛教方面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吐蕃传统思想——苯教并没有因此而偃旗息鼓、解盔弃甲,而是厉兵秣马,积蓄力量,寻找一切机会向佛教反攻。静命论师到藏后,“在隆促宫中,由阿年达任翻译,(向赤松德赞等人)讲述‘十善业’、‘十八界’及‘十二因缘’等法门。”(30)恰值此时,吐蕃地区发生了多种灾害,诸如“水卷旁塘宫堡,雷击红山,人疫畜病以及天灾。因此全体属民心生反感。”(31)这些便成了那些不信佛教的传统势力反对佛教的把柄。有人说,这些灾祸都“因赞普推崇佛教所致”,有人说“是作佛法所得的恶报”,有人说是因佛教的教义“触怒了藏地的邪恶鬼神”所引起的,要赞普下令让印僧返回尼泊尔。在这咄咄逼人的挑战面前,赤松德赞王不得不让静命返回尼泊尔。
静命在吐蕃的传教受挫,并没有动摇藏王赤松德赞坚持和发展佛教的决心。他又派人去乌仗那(今克什米尔)迎请密咒大师莲花生前来“调伏魔障,显扬佛教”。莲花生一到吐蕃即用佛教密宗中的那套类似于苯教巫术的咒法,将苯教的许多自然神灵接纳到佛教密宗中,宣布为佛教护法神。例如莲花生在进藏途中遇到“念青唐拉(神山)以其巨大神变之身挡住去路,于是(莲花生)阿 黎即以手杖压之,随使念青唐拉变成为乾闼婆文殊菩萨”,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另外,莲花生还尽量利用仿效苯教驱鬼摄魔、祭祀神灵的那套宗教仪式,并把它吸收到佛教密宗的巫术中。例如莲花生进藏沿途“施于鬼神的朵玛(祭鬼之食品)”及所举行的火祭仪式都来自苯教的祭祀仪式。更为有趣的是,在莲花生的倡导下修建的桑耶寺,“寺内的菩萨像,系仿照藏人的形象塑造的。”(32)关于这个情况,《贤者喜宴》一书中有比较详细的记载。在桑耶寺的修建过程中,“雕塑佛像的工匠说:印度、汉地之中选哪国的风格塑造佛像?请赞普、众臣、堪布商议。这时堪布说:佛出自印度,故按印度之风格塑造佛像为宜。赞普说:还是按吐蕃的风格建造,这样做对诸贪恋苯教的藏人希望他们改信佛教有益处,所以要按照藏人的形象塑造佛像。遂召集全体藏人,以藏人的模样塑造了诸佛、菩萨像。其中选出了形体优美的库·达财为模特儿,主要建造了阿利耶巴海洲喀热萨波尼;以唐桑达龙为模特儿,右面造六字真言;以玛桑贡为模特儿,造护门神马头明王;以美丽绝顶的王妃拉波漫为模特儿,右边造度母像;以王妃诺琼为模特儿,左面建造了具光佛母像。”(33)这是赤松德赞采取的佛教藏族化的一个重大举措。
静命和莲花生两个外地人在吐蕃传法,一个遭到了失败,一个取得了胜利,原因何在?还有赤松德赞王为什么以藏人的形象来塑造佛像和菩萨像?
这是因为莲花生为了确保佛教能在异域的土壤中扎下根来,一踏上西藏的土地,就根据西藏政治、思想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阐发了佛教思想,即把藏族人熟悉的神祗、仪式等纳入了佛教中,将这种改变了形态的佛教传播到西藏,以适应藏族人的心理、习俗,促使更多的藏族人熟悉佛教、了解佛教,这样藏人即能用对待苯教的眼光来看待佛教,以消除对佛教的陌生感,为佛教在吐蕃地区的传播扫清了障碍,也为后来佛教在西藏的发展找到了一种途径。
但佛苯之间的斗争并没有绝迹,当建桑耶寺时,苯教徒及其崇苯官员抗议说:“勿行佛教,当行苯教”(34),而代表佛教一方的寂护就说:“一国之内若行两种宗教,此情极恶。(35)我等当辩论,如你获胜,我便离去,你们随即发展苯教;假若佛教获胜,则应废弃苯教,而弘扬佛教。”于是一场佛苯之间的辩论在藏王赤松德赞的支持下开始了。佛教一方为祥尼雅桑等四人为代表。藏史记载,在辩论中“苯教起源恶劣而且(辩论)理由微小无力。但是佛教起源高尚(辩论)之理由深广有力,论诤出色,智慧敏锐,不可战胜”。(36)这样,佛教以自己理论的深奥,衬托苯教思想的粗浅,辩论以佛教的胜利而告终。赞普亲自宣布大力弘扬佛法,苯教无理,应为弃,并决定:
1以后“不得施行苯教”。
2“不准为死者宰杀牛马及牲灵,不得放置肉类”。
3“凡为诸王消祸禳灾,如果对妖魔想举行苯教法事,蔡米及香雄两处外,他处不得做此法事”。接着又把“苯教书籍悉数投于河内,余者最后均以黑塔压之”。
这是佛苯之间的第二次交锋。在佛苯第一次交峰中赤松德赞以强制手段剪除了崇苯反佛的权贵,例如仲巴杰被坑埋,达扎路恭被流放,为藏王赤松德赞建树佛教打开了方便之门。这次则以辩论方式从理论上战胜了苯教势力,进一步巩固了佛教在西藏的地位。
此后在莲花生大师的主持下,兴建了桑耶寺作为根本的道场,这是西藏佛教第一座有出家僧人住寺修行的寺院,先度七比丘随后有三百余人出家为僧,并“由菩提萨垛作他们出家的亲教师”这便是佛教在西藏建立自己的僧伽组织的开始。在这个时期,赤松德赞集中了印藏译师,“翻译了许多佛典”。为了避免译经重复,把译出的经论编定三个目录,即《庞塘目录》、《秦浦目录》、《登迦目录》。前两种已经佚失,后一种即包括六、七百种译出的经典。为了适应翻译
人员的工作需要,还编纂了《翻译名义大集》这样一部梵藏对照字汇的工作手册。又“迎请持密大师大摩根底、在伏摩密寺中,传授《瑜伽金刚界》等大曼茶罗灌顶,由迦湿弥罗的班智达枳那弥遮,乃达那西等师在净戒寺传授戒律,由汉地和尚在不动禅定寺净修禅定;在修祠楚寺作修词学,在格卓白哈寺安置财物,在毗卢遮那寺中讲说佛法。完成如此种种事业,使佛法圆满地兴盛起来”。(37)总之,赤松德赞王“对于整个佛教尽量吸收,不论大小,显密、讲修兼收并容,盛极一时”。(38)后来阿底峡尊者赞颂这一盛况时说:“尔时佛法兴盛,于印度似亦未有也”。(39)到了赤松德赞王的晚年,汉地的禅宗思想传到了吐蕃地区,其代表人物就是摩诃衍那,摩氏是活动在沙州一带的一位禅师,早年在长安修业,师从禅宗之大师。据敦煌文献记载,他“一生以来唯习大乘禅”。大约是在781年前后,应赤松德赞王之诏令来到吐蕃传播禅宗思想。没有多久,摩诃衍那的禅宗思想在广大的吐蕃人中备受青睐,十分走俏,广为弘扬,而寂护等人在吐蕃传播的印度的大乘中观思想则每况愈下,极受冷落,以至于使昔日香烟燎烧、晨钟暮鼓的桑耶寺中出现了香火中断,善业不存的惨景,在这种情况下赤松德赞王作出了一个特别的决定:用汉地禅宗思想与印度佛教思想辩论的胜负来决定其在吐蕃的去留问题。据藏史记载双方经过了三年的充分准备后,即在赤松德赞王的主持下进行了辩论,辩论的内容在很多藏文佛教论著中都有详细的记载,著名藏传佛教专家法尊法师作了简要而准确的概括,现抄录如下:
首先由摩诃衍立宗:“行诸善业往生善趣,行不善业,堕诸恶趣,故彼二业,皆不能出生死,且障成佛。譬如白云黑云,俱蔽晴空,若都能无所思,即能解脱生死。由不作意思,即无所得,故顿悟者与十地相等”。(40)摩诃衍那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后,即由印度佛教的代表莲花戒对其观点进行了驳斥:
“若都无观察慧,诸瑜伽师由何因缘能住分别耶?若谓是不念一切法者,然一切所修皆不能不念及不作意。若谓我今不念诸法,是则已念诸法。若谓无念心所即成无分别者,则闷绝昏-迷之际亦应是无分别也,若无正分别,则别无入无分别之方便,仅灭念心不分别诸法,为何能入一切诸法皆无自性耶。既不了达性空,即不能断诸障,故是要以正智方能断除颠倒错乱。又若无念无作意,云何能成宿住念通及一切种智,复云何能断诸烦恼,以是瑜伽师以正智现证真义者,是由了达内外三时一切皆空,乃能灭诸分别,离诸恶见也”。(41)
辩论的结果是以摩诃衍那为首的汉地禅宗败北,以莲花戒为首的印度佛教取胜。最后印度佛教作为当时吐蕃王朝正统的意识形态继续在吐蕃弘扬广大,而以摩诃衍那为首的汉地禅师们则被迫离开了吐蕃。对这一情况,土观大师在其名著《宗派源流与教义善说晶镜史》一书中作了比较简要的说明:“到了赤松德赞王晚年,有摩诃衍那和尚从汉地来藏,倡言非但应舍不善分别,即诸善品分别,亦是能缠缚生死,无论铁锁金锁,同属缠缚,只应全不作意,才能求得解脱。倡此邪见,藏众翕然风从,往昔菩提萨诃等所教导的清净见行能行持者日益渐少。藏王欲破此邪说,遂派人迎请善巧之王莲花戒论师入藏,与和尚辩论,击败了他。为引据正理,破他的邪见,造了《修次第》三编,使清净的见行,又得重光于世”。(42)这样,中观自续派便成了藏传佛教前弘期的主要思潮。
四、墀热巴巾王扩充佛教
热巴巾王时期是佛教的高度发展时期,他的主要功绩在于为了翻译佛教经典的需要,统一了文字,统一了译名、统一了译例。整理的译典“收录在书目中,因之,三藏教典得以大备”。在译经方面,他规定除根本说一切有部的佛经之外,凡未经指定者均不得翻译,密咒诸经典不得翻译。
热巴巾还规定,对前代所建的寺院善加修葺,七户庶民赡养一僧;对侮慢三宝者刑罚特重,即凡之后置僧人者割舌,恶心指僧人者截指,怒视僧人者剜眼。他还将头巾置于坐垫上,让出家僧人的双脚置于其上,以示对僧人的尊重。另外,藏传佛教史上的寺院经济也是从墀热巴巾王时期开始的。据江浦寺前所立石碑记载:“神圣普天子可黎可足猎赞陛下之鸿恩,遇聂多极隆,为仰报赞普之恩眷,回向赞普陛下之功德,广为祝祷延福,乃于堆垅之江浦,建神殿,立三宝之所依处,敬事四部比丘等众。作为供奉顺缘之奴隶、农田、牧场及供物、财产、牲畜等项,一应备齐,悉充赞普可黎可足猎赞之常川不断之供养功德。(43)据此,在赞普热巴巾以前,佛教僧人只有奴户,没有土地、牧场、牲畜等。到热巴巾时期,对一些寺院赐给了土地、牧场、牲畜等,从此,藏传佛教便遂渐具有独立的寺院经济。这就为以后藏传佛教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热巴巾采取的这些措施,使佛教在西藏得到进一步发扬,也引起了一部分臣民及传统势力的不满。有人说:“不杀国王不能毁灭教律。”有人说:“即使杀掉国王,王子藏玛及大臣甄卡贝吉云丹二人也爱佛法,教律仍不能破坏。”最后导致了热巴巾遇害、朗达玛灭佛
的事件。
五、朗达玛王毁灭佛教
佛教与苯教的第三次斗争是在朗达玛上台以后开始的。热巴巾王被杀后,朗达玛继赞普位。他一上台即视佛法为洪水猛兽,异端邪说,竭力打击,从而掀起了第三次灭佛狂澜,其规模比第二次禁佛运动要大得多。这次禁佛的主要措施有以下几点:
1封闭和拆毁了佛教寺院;如“大昭寺及桑耶等寺的门堵塞,余下之一切小神殿尽毁之。”
2焚毁了佛教经典,如“佛典或投之于河,或焚之以火,抑或埋于沙沟内”。
3镇压了佛教僧人,如“著名僧人被杀,次等僧人被流放,低级的僧人被驱使为奴”。
吐蕃的佛教势力由此一蹶不振。虽然这次禁佛运动时间不很长,但是对佛教的打击是非常沉重的,到了“藏地佛教遂全被毁灭”,佛法几乎不传的程度。
藏史把这个时期称为“灭法期”或“黑暗时代”。这样的一个时代给藏族传统思想——苯教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六、前弘期藏传统佛教的主要思想
前弘期藏传佛教的主要思想藏传佛教前弘期的佛教思想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中观思想盛行,汉地禅宗思想流传,密宗思想风靡,从而在藏传佛教界形成了三足鼎立的格局。密宗思想将在宁玛派的佛教思想一章中详细论述,这里着重论述中观思想和禅宗思想。
(一)汉地禅宗思想流行一时
首先是心性本净的佛性论。
汉地禅定堪布圣珠言道:“所谓大乘见即是:世间一切有为法皆为无为法,它无始清净且平等。”(44)堪布提悟禅师说:“心性既已洗濯无需水,既已布施无需财,如以清净心修得了正法,由于真实故,遂可得如来。”(45)在这里“性”是指人心的本性,他们的逻辑是:心—性—性—佛。这就是说人性和佛性是没有任何差别的,清净心(即佛性)内在地、先天地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不需要以后天从外面人为地洗涤或布施。只要你定心修得了佛法,就可证得真如成为佛了。这样,他们就把心和佛等同起来了,这与禅宗提出的“即心即佛,心佛不二”的本体论命题同一鼻孔出气。
其次是无思无为的顿悟成佛法。
摩诃衍那说:“善者转为善趣,恶者转为恶趣,迨破除身语一切善恶意念之后,则顿时可入无念之道。”(46)他还说:“无需修习身语之法,不会因身语之善业而使人成佛,修得无念、无思即可成佛。”(47)这是说怎样才能顿悟成佛呢?摩诃衍那认为唯一的方法是“无念”,即成佛的工夫在于修得“无念”。“无念”是摩诃衍那顿悟理论的主要范畴,其意思是说不管是好的念头还是坏的想法均是成佛的障碍,只有无思无为才是成佛的唯一方法。
再次是不立文字的快速成佛法。
汉僧摩诃衍那说:“文字之中无精义,名言佛法不成佛。若自心觉悟,则系唯一白法,是故当以此(论)为妥。”(48)他还主张不须修法以扫除文字障碍,但凭静坐睡卧,徐徐入定,方寸(心)不乱,便可直指人性,体验佛性(49)。这就是主张不立文字,不研究和学习佛典,只要悟得佛性本有,就能顿悟成佛。
以摩诃衍那为首的汉地禅宗师徒们被赤松德赞王扫地出门了,但其思想的余韵流波曾长久地影响着后弘期以来的藏传佛教诸宗派的教义思想。土观大师说:“心要派汉人呼为宗门,就其实义与噶举派相同,即大手印的表示传承。”(50)阿芒·贡确坚赞大师说:“大手印及大圆满的名称虽不同,然修习者们在修持时任何亦不作意与汉地摩诃衍那之(思想)相同。”(51)阿芒还说:“莲花戒在《观修三次第》中破斥的摩诃衍那的诸教理与后弘期之大圆满法和大手印法相同,就像摩诃衍那离开吐蕃时在此地留下了一只鞋一样。当前红帽派们自诩是宁玛派,并认为大手印法和大圆满法无异,二者之中像摩诃衍那和尚的做法很多。”(52)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大师说:“只依汉地堪布教理之文字,隐去彼之立名,变为大手印之名。现时之大手印,基本上都是汉地之佛法(指禅宗)。”(53)“有很多大手印和大圆满等新旧派们,将修习性空立名为会到心之本面。”(54)藏传佛教大师们的这些说法即清楚地说明,后弘期以来形成的藏传佛教诸宗派的教义已深受摩诃衍那禅宗思想的熏陶、浸润,尤其是对晚期宁玛派的大圆满法和噶举派的大手印法影响更为深广。据藏史记载,像宗喀巴这样的佛学大师,在学习佛法的初期亦深受摩诃衍那禅宗思想的影响。土观大师说:宗喀巴当时“颇满足于全无所许和不取任何境界之见。”(55)所谓“全无所许”和“不取任何境界”的意思是说,不缘善,亦不缘恶,排除任何思念,使自己的心态处于死寂状态,这便是典型的摩诃衍那的禅宗思想。
(二)中观自续派见独步佛门
藏传佛教前弘期在吐蕃占主导地位的佛教思想是静命、莲花戒所持之中观自续派见。对此,土观大师作了全面的说明:“关于前弘期的正见,初藏王赤松德赞时,曾首次向全藏宣布法律:凡诸见行,皆应依从静命堪布传规。和尚事后,王又重为宣布,谓今后正见,须依龙树菩萨之教,若有人从和尚之见者,定当惩罚。由此原故,在前弘期,虽有少数唯识派宗见的班智达来藏,然主要的仍然是静命堪布及莲花戒论师之风规,属于中观自续派见,此派较为发达。”(56)
所谓“中观”,即是“脱离常断二边的中道观”。因为“一切有部、经部、唯识三个宗派堕入了执著法之边见故,未能超出执著之戏论。此宗则依据中转法-轮之一切经典,一切法不落常断之任何一边,承认其中道,所以称为中观宗。”(57)另外,此宗认为“一切法都没有真实存在的体性,所以称为说无自性宗。”(58)总之,将一切法的现象理解为缘起有,本质理解为离八边戏论之自性空,即是中观见。此宗见依世俗和胜义二谛的建立为本体,圆满通达了人无我和法无我的真谛(59)。中观宗又分为中观应成派和中观自续派。藏传佛教前弘期在吐蕃地区传扬的是中观自续派,故这里主要介绍一下中观自续派的思想。
中观自继派的根本观点是:“一切诸法于世俗错乱思想者之识中皆有,而于胜义无错乱思想者之慧中则皆无,即说自续中观之所。”(60)《宗派建立宝论》中说:“主张就名言的范围而言,诸法皆以自相而存在的说无自性宗,就是自续
派的定义。何以称为中观自续派?因为此派主张凭借真正的因,此正因由存在的三条原则所构成,就能破除一般人认定诸法真实存在的错误观念,所以称为自续派。”这是说在世间名词、概念的范围内,一切事物和现象皆有独立自存的意义和内容,所以构成正因的三条原则(即遍是宗法性、同品定有性、异品遍无性)也有其自相。
自续派的本质是,“由对方所许实执之诸边由道理(即指概念、判断、推理)破除之,尔后于其原址上成立心之自性离戏论如幻”的真谛。这是说中观自续派的主要特点是,在方法论上主张必须运用因明的原则和论轨,立出正确的因量,即在破论敌时首先要提出自己的正当理由,要用概念、判断、推理的论式,才能使对方了解己方的观点,有效地破他立己。
既然要用因明的论轨来破他立己,则因明的宗、因、喻三支中的因支,必须具足三条原则,即遍是宗法性、同品定有性、异品遍无性,然后才能构成一个正确无谬的因。因为自续派主张破他须自立量,因此不得不承认自立之因、喻是实存的。只有先肯定了这点,立量才有意义,否则,一说无自性便自语相违。既然要承认因的实在,那么就只好主张构成正因的三条原则也是有其自相的,而不是假名施设的了。这就是自立量派,即中观自续派。中观自续派又分为:
“瑜伽行中观自续派、经部行中观自续派二种。不许外境而许自证分之中观师,此为第一派之相。所相者,如静命阿 黎。不许自证而许外境由自相成就之中观师,此即第二派之相。所相者,如清辨阿黎。亦有释义,若所许根本之建立与唯识宗相顺,即瑜伽行中观派;若如经部许极微积集为外境事,则谓经部行中观派。瑜伽行中观自续派亦有与相实派相顺之中观派及与相假派相顺之中观派二种。
第一、如静命、莲花戒、圣解脱军。
第二、如狮子贤、祗多梨、罗瓦巴(毳衣师)。说祗多梨与相假有垢派相顺,罗瓦巴与相假无垢派相顺。”(61)
在西藏佛教的前弘期,流行的主要思想是瑜伽中观派。此派的方法论和对二谛的解释,是承袭清辨一系的自立量派,不同于月称一系的随应破派。瑜伽中观派的创始人是静命论师(亦称寂护),他是8世纪东印度人,曾任那烂陀寺主讲,他与智藏、莲花戒被誉为清辩以后“东方自立量派三大家”。其中的静命和莲花戒与西藏前弘期佛教关系极为密切。静命的主要著作是《中观庄严论》,莲花戒的主要著作是《中观光明论》、《修道次第论》等。
明确地把瑜伽行派学说和中观学说结合起来的是静命。关于瑜伽行派思想和中观思想的融合,早在公元8世纪时,传为弥勒所著的《现观庄严论》中,就已经出现了“以胜义无自性空为基础兼采若干瑜伽观行以组织学说”的趋势,后来静命明确地把瑜伽行派“唯心无境”的学说纳入中观派的体系中,因而被尊崇为瑜伽行中观自续派的创始人。静命在其著作《中观庄严论》一书中批判了各家学说的缺陷后,提出了应从“唯心无境”的观点出发,才能真正理解到法无自性的道理,这是瑜伽、中观二派都应掌握的,因而二家应该合二为一。这样,静命就将唯识说吸收到中观宗的体系中了。
具体讲,静命的瑜伽行中观派思想的发展过程是这样的:瑜伽行派首先主张“唯心无境”说,肯定了内心的真实存在,否定了外境的真实存在,继而再进一步说,心亦不可得,把心的真实存在也给否定了。中观自续派的代表清辨反对瑜伽行派的这一观点,认为与其先说有,后说无,还不如直接说二者均无。静命吸收了清辨的这个说法,说在世俗谛里,是唯心无境,在胜义谛里,心境俱无,这便是静命学说的关键所在。
静命与西藏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藏王赤松德赞将静命论师邀请到西藏传经说法,建立寺庙,组织僧团,降伏苯法,为建树和发展西藏佛教立下了汗马功劳。自然,静命的瑜伽中观派思想在当时的西藏佛教界也就风行一时了。
瑜伽中观思想和藏族传统的“本无空寂”论虽然论题各异,但其旨趣非常接近。因此,似应这样看,“本无空寂”的思想为中观宗在西藏的传播准备了思想土壤,架设了精神桥梁,而中观宗思想的传播和发展又丰富和深化了“本无空寂”的本体论思想,二者是相资为用、相得益彰的关系。
注 释:
(1)王忠《松赞干布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6页。
(2)3)(12)(13)(14)(16)(19)(23)(24)(25)(26)(27)(28)(29)(30)(31)(33)(34)(35)(36)(46)(47)巴卧·祖拉陈瓦《贤者喜宴》,民族出版社1986年藏文版,第171、184、185、303、304、305、309、316、332、334、376、382、383页。汉译主要参照了黄颢先生的译文。
(4)(6)《拉达克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藏文版,第31页。
(5)(9)(10)王尧、陈践《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第161、165页。
(7)(8)根敦群佩《白史》,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1990年藏文版,第253—254页。参照傅师仲译文。
(15)柏克韦施《吐蕃与欧亚大陆中世纪初期的繁荣》,《藏学研究译文集》第二集,中央民族学院藏学研究所1983年铅印本,第66—72页。(17)(32)(37)布顿仁钦朱《佛教史大宝藏论》,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第170、174页。
(18)(38)(39)法尊《西藏前弘期佛教》,载《中国佛教》(一),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第134、173、138页。
(20)(22)萨迦·索南坚赞《王统世系明鉴》,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1页。(21)(49)黄奋生《藏族史略》,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55—56、71—72、116页。(40)(41)法尊《西藏民族政教史》。
(42)(50)(55)(56)土观·罗桑却吉尼玛《宗教源流与教义善说晶镜史》,甘肃民族出版社1984年藏文版,第50—51、267—268、439页,汉译主要参照了刘立千先生的译文。
(43)王尧:《吐蕃金石录》,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第180页。
(44)(45)欧坚朗巴掘自雅隆石窟《五部遗教》,民族出版社1986年藏文版,第460、461页,笔者译。
(48)巴色朗《巴协》,民族出版社1980年藏文版,第72页,笔者译。
(51)(52)阿芝·贡确坚赞《萨迦、宁玛、噶举诸宗派见地之差别略议》,民族文化宫图书馆藏文藏书,第39、46页,笔者译。(53)(54)萨班·贡噶坚赞《三律仪论说自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藏文版,第87页,笔者译。
(57)措如·次朗《宁玛派教法史》,民族出版社1989年藏文版,第77页,笔者译。
(60)郭若扎西《郭扎佛教史》,中国藏学出版社1990年藏文版,第74页。
(58)(61)晋美汪波《宗派建立宝论》,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铅印本,笔者译。
(59)土丹尼玛《宁玛九略述》,载《藏学研究论文集》宗教类,民族出版社1991年藏文版,笔者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