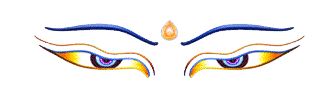《菩提道灯难处释》探微
陈玉蛟(释如石)
提要
阿底峡的《菩提道灯难处释》(以下略作《难处释》),是属于「道次第」一类的论典。因其内容偏重宗教实践,没有严密的逻辑论证,没有庞大精深的思想体系,读起来并不费力。因此,本文只拟探讨此论释的「版本」、「真伪」、「特色」、「对西藏佛教的影响」、以及「与《菩提道次第广论》异同之辨」等几个问题,希望藉此能对《菩提道灯难处释》得一全盘的了解。
研究的结果显示:
1、北京版《西藏大藏经》的错误率较德格版高。
2、《难处释》中的一小部分,可能是那措译师根据阿底峡口述增添的,并非阿底峡亲笔所撰。
3、「三士道」之说,源自《俱舍论释》与《摄抉择分》,非阿底峡首创。
4、《难处释》有下列六项特色:
(1)在一般归依的基础上,强调不共的大乘归依。
(2)在菩萨戒方面,以无着的《戒品》为主,以寂天的《学处集要》为辅。在持戒要领方面,强调「幻化观」和「自他换」。
(3)在定学方面,重视神通,借神通之力,迅速圆满福德资粮。
(4)在慧学方面,偏向中观应成派而兼含自续思想。
(5)贯通大乘显密二宗。
(6)重视实践,广引百多部经教和论典。
5、《难处释》含摄了当时印度盛传之学,更结合了实践与教理二轨,为西藏佛教提供了最正确的走向。而月称中观应成派的学说,能在西藏受到重视,并继续发展,《难处释》的引介功不可没。
6、《难处释》与宗喀巴根据此论释撰写而成的《菩提道次第广论》,约有六处较明显的差异。其中最值得注意的一点,就是《广论》将《难处释》中作为行菩提心的「增上意乐」,移到「愿菩提心」之前,形成了「七因果发心」说。
一、前言
根据西藏史料记载﹕自从西藏朗达玛王(Glang dar ma)大肆毁灭佛教以后(838~842A。D。),西藏的前弘期佛教遭到非常严重的破坏。佛寺不是被拆毁便遭封闭,僧团组织解体,翻译和学经的活动完全停止。如此,大约经过一个世纪左右的「黑暗时期」或「灭法时期」。到了公元十世纪后半,政治风暴平息,社会逐渐安定以后,西藏佛教才重新获得恢复的机运,并从此展开更为生气蓬勃的「后弘期佛教」。而在后弘西藏佛教的发展中,影响最大、贡献最巨的印度高僧中首推燃灯?吉祥智──阿底峡尊者(Dipamkarasrij-nana--Atisa,982~1054)。
阿底峡应藏王智光之请,于一○四二年去到西藏弘法,前后一共居住了十三年。在这十三年间,他借着大量的传法、讲经、翻译和著述的活动,将毕生所学、所证的大乘佛法的精要,倾囊传授给求法若渴的藏人。阿底峡一生著作丰富,有显有密、有观有行,西藏大藏经中就收录了一百多部他的作品。而其中观行兼备且对西藏佛教影响最大的,首推《菩提道灯》(Byan chub lam sgron)及其自注──《菩提道灯难处释》(dka”grel)。因为这部论和自注是阿底峡针对当时西藏佛教界弊害而写的,而且经过弘传以后,有效地整顿了后弘初期西藏佛教紊乱的教理与躐等的修习次第,使西藏佛教步上教理系统化与修持规模化的正轨。自此以后,西藏佛教有关修道次第一类的论著,大多以《道灯》及其自注为蓝本。例如﹕噶当派卓垄巴(Gro lung pa)的《教次第广论》和《道次第广论》﹔噶举派冈波巴(sGampopa,1079~1161)的《大乘菩提道次第解脱宝庄严论》(Thal rgyan)和宗喀巴(Tsong kha pa,1357~1419)的《菩提道次第广论》(Lam rim chen mo)等等。
《难处释》是《道灯》的注释,《道灯》义理不明的地方,释中都作了简要的说明。释中除了提示戒定慧三学的各项修持要领之外,更举出一百多部与修持相关的重要经论,为修学者指出研读经论的方向,完善地结合了教理与实践。这一点,对西藏佛教日后解行并重的发展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总之,阿底峡及其《道灯》、《难处释》,对西藏后弘期的佛教影响极其深远。因此,想要了解西藏后弘期佛教的源流,研究阿底峡的生平、思想、修持宗趣以及《道灯》、《难处释》两部著作,实为最重要的一环。此外,阿底峡是十一世纪初印度超戒寺著名的高僧,研究他和他的这两部著作,也有助于我们对十一世纪印度佛教的认识。以上就是笔者撰写本文的动机。
二、关于版本问题
本书翻译《菩提道灯》及《难处释》,系根据北京版与德格版两种版本。由于这两种版本在文字上有不少的岐异,因此在进行翻译研究的同时,笔者曾将此二版本加以比对,列出彼此歧异的字句,作成一个「对勘表」(参见《阿底峡与菩提道灯难处释》玖)。并且根据文法规则、前后文义以及其它相关文献尝试作一正误的抉择,正确者以「○」表示。从「校勘表」中,笔者发现到如下几个问题﹕
1、北京版错误率偏高﹕
「校勘表」总共列出两版本岐异处700条。其中,两版本同时都有问题的很少。在700条岐异处中,北京版有560条是错误的,约占全数的80%。
2、北京版的岐误有四种类型
(1)具格的kyis,gys,gyis等,经常被写成属格kyi,gi,ghi等。这种情形出现的次数最高,共有70条,约占北京版错误总数的12.5%。
(2)属格的kyi,gi,gyi等,也经常被写成具格kyis,gis,gyis等。这种类型的错误共有45条,约占总错数的8%。
(3)其它较常出现的型态是﹕在德格版中未来式“g”前音的动词,常被写成的“b”前音。这种情形总共有11条。如
a。gzung→bzung
b。gzhag→bzhag
(4)北京版有多出一整句或一整段的情形。详见《阿底峡与菩提道灯难处释》玖、「《菩提道灯释》校勘表」(注1)。
总而言之,德格版与北京版丹珠尔都有差错,都不完美。不过,二者相形之下,德格版总算比较可靠。至于,为什么北京版的错误会这么多﹖会出现特定型态的错误﹖这两个问题,已经超出本文的研究范围。在此不拟讨论,留待异日另行处理。
三、《难处释》真伪之辨
阿底峡刚到西藏不久,就答应菩提光的劝请,写作了《菩提道灯》。这一点,传记上有明确的记载﹕而且《菩提道灯》的最后一颂也有明文(注2),因此,从来没有人怀疑过它的真实性。但是《难处释》就不同了。宗喀巴在《广论》中指出﹕一般的传记或史料上都不说阿底峡自造《难处释》﹔只提到﹕阿底峡在布让(sPu rang)时曾经作了一个略释,后来住锡桑耶的时候,戒胜译师请求阿底峡进一步作更详细的增释。阿底峡说﹕「你自己发挥添加就可以了。」所以,戒胜译师就根据尊者所作的略解,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添加进去,而成为今日丹珠尔中的《难处释》。因此,《广论》中毫不隐晦地指出《难处释》中有数处误谬(注3)。
《难处释》中有那些错误,《广论》并没有一一指出。唯一被提出来讨论的,就是关于「发心学处」的问题。《难处释》中说﹕印度诸大学者对于「发菩提心学处」的看法并不一致,共有四种不同的看法。有人主张﹕「发心学处」是初发心者及趣入行者所有的学处。也有人主张﹕应该守护经典里面所说的一切学处等等(注4)。宗喀巴认为﹕这两种说法不可能是阿底峡自己写的,不足以采信。因为所发的心如果是行心,那么只在归依学处上,外加取舍白法和黑法等八法来作为「发心学处」,这一定是不够的。如果发心只是愿心,那么就不须要学习经里面所说的一切,以及趋入行持以后的所有学处。否则愿心和菩萨戒的学处就没有差别了(注5)。
笔者认为,宗喀巴的立论不一定能成立。因为阿底峡一生广泛参学,博闻强记。因此,在强调实践的《难处释》中,广引众说,聊备参考,并非不可能。尽管如此,宗喀巴这种慎思明辨的研学态度,的确值得钦佩与学习,而他在《广论》中所提出的这项质疑,也值得留意和进一步探究。
四、「三士」说非源自《菩提道灯》
《菩提道灯》第2、3、4颂说,众生的根机有三种,即下、中、上「三士」。因此,有些学者便误认为﹕「三士」的观念和说法,肇始于阿底峡的《菩提道灯》。如「宗喀巴的《菩提道次第广论》」一文中说﹕「本论是根据《菩提道炬论》所说的三士道的次第而组织的。」(注6)《西藏佛学原论》也说﹕《菩提道灯论》判别众生根基为﹕下士、中士与上士(注7)。这样的说法,表面上看来似乎没有什么毛病,但是很容易造成一般读者的误解,使人认为﹕「三士道」是阿底峡的创见。例如﹕有人在「阿底峡的佛学思想及其对西藏佛教的影响」一文中说﹕「尊者将佛法总摄为三士道。」《望月大辞典》里面的说法,也不例外(注8)。
其实,《菩提道灯》「三士」一词及其概念,出自世亲的《俱舍论释》。阿底峡在《难处释》中,引用世亲的《俱舍论释》说﹕
「下士,想办法追求自己的安乐。中士,只求灭苦……。上士,由于自己有痛苦,所以只图为他人求取安乐,根除痛苦。」(注9)
由此可见,《菩提道灯》中「三士」的名称和定义,完全根据《俱舍论释》,非阿底峡的创作。事实上,「三士」名称与概念的形成,恐怕比世亲的时代还要早些。因为《瑜伽师地论》「摄抉择分」说﹕
「复次,依行差别建立三士,谓上中下。无自利行无利他行,名为下士。有自利行无利他行﹔有利他行无自利行,名为中士。有自利行有利他行,名为上士。」(注10)
由此可见,早在无着与世亲时代,「三士」之说已普遍流传于部派佛教学者与大乘瑜伽师之间。阿底峡只不过是引用此说,强调唯独上士才是大乘法器,才是《菩提道灯》最主要的开示对象而已。
五、《难处释》的特色
(一)强调大乘归依
一般所谓归依,是指有人深感三界痛苦,无依无靠,因而归投三宝,祈求三宝庇护,并导令解脱。这种归依,适用于所有初入佛门的一般弟子,也是归依的最原始意义。因此,进行归依仪式时,只要简单地口诵如下的「归依文」就够了﹕
「我某甲,尽形寿归依佛﹔尽形寿归依法﹔尽形寿归依僧。」(注11)
然而,《难处释》中所说的,不是这种简单的归依﹔而是在一般归依基础上,更上一层楼的大乘归依。如《难处释?大乘归依》中说﹕「某人已决意出离轮回的痛苦,经常忆念死亡,心性慈愍,心智聪慧,而且不曾违犯七众别解戒中的任何一种。又,初夜、后夜皆不睡眠,勤修瑜伽,饮食知量,护诸根门,戒慎恐惧,恐犯细罪。这样的人心想﹕“…听说有一种称为大乘的佛法,能究竟自他的利益。我应该找寻一位最殊胜的善知识,从他那里求得这种大乘佛法。”」(注12)
既然是为了追求自他利他的大乘佛法来求受归依,而大乘佛法的终极目标又是无上菩提﹔因此,《菩提道灯》便主张﹕大乘归依须以「不退无上菩提之心」为动机,再配合《圣普选行》的「七支供养」去行归依的仪式(注13)。这种大乘归依的观念与型式,在阿底峡以前的论典中,似乎还没有提出过。果真如此,那么在一般归依的基础上,强调更进一步求受大乘归依﹔应该是《菩提道难处释》的特色。
(二)菩萨戒学以无着为主寂天为辅
在大乘的菩萨戒学方面,阿底峡主张﹕大众别解脱戒是受持菩萨戒的基础、前行。因此,在受学菩萨戒以前,应该先具备任何一种七众别解脱戒。不过,较诸别解脱戒,阿底峡似乎更重视大乘种性或宿根。如《难处释》中说﹕
「已住于种性和已经在他生修习过大乘的人,自然不做恶事。因此,这些人虽然一开始就受菩萨戒也没有过失……。受戒前没有大乘气习的人,(即使受了戒)也生不起菩萨律仪。」(注14)
具备了别解脱戒的基础以后,有心修学大乘佛法的人,应该进一步求受菩萨戒。菩萨戒的受戒仪轨,有有师和无师两种。这两种仪轨在唯识开宗祖师──无着的《菩萨地》「戒品」和中观学者寂天的《学处集要》(‘siksasamucarya)中都有。《难处释》在有师仪轨方面,采取「戒品」的说法,在无师仪轨方面则根据《学处集要》(注15)。至于阿底峡为什么会做这样的选择,《难处释》中并没有说明。难道是为了调合无着和寂天(’santideva,约650~700)的菩萨戒学说吗﹖我个人认为﹕主要的原因可能是为了截长补短。因为有师轨,「戒品」说得完整﹔而无师轨,则《学处集要》中介绍得较为详细。
此外,有关「戒的种类」、「舍戒因缘」、「不舍戒因缘」、「出堕」以及「持戒的利益」,《难处释》中也将无着与寂天的学说并列,先介绍「戒品」的说法,再引用寂天的学说作补充(注16)。至于「持戒要领」,阿底峡完全采取中观宗的幻化观、和寂天从「缘起相依相待」的理念所发展出来的「自他换」修法,修习念死、念戒、正知、正念、不放逸、忏悔、随喜和回向等项目(注17)。
总之,《难处释》以无着的「戒品」为架构,辅以寂天《学处集要》的学说,再配入「幻化观」和「自他换」的持戒要领。这无疑是《难处释》菩萨戒学的一大特色。
(三)定学重神通
在《难处释》的「增上定学」中,阿底峡特别强调引发神通的重要,并且主张﹕神通是利他和圆满两种资粮的最佳方法(注18)。如说﹕
「如鸟未长翼,不能空中飞,若离神通力,不能利有情。俱通者一日,所生诸福德,诸离神通者,百世不能集。」(注19)
此外,更引用其师菩提贤(Bodhibbadra)的《定资粮品》(Ting nge'jin tshogs keyi le'u)及龙树的说法来成立自己的主张(注20)。
在早期的显教论典中,提到引发神通可以利益众生的说法尚易见到,但是特别强调“神通是圆满福德与智慧两种资粮之因”的教典就少有了。阿底峡之所以会如此重视神通,可能与当时密教的流行有关。因为《难处释》「密咒乘」中说到﹕借着念诵和禅定修成息、增、怀、诛和世间八大悉地以后,就能迅速不费力地圆满福德与智慧两种资粮(注21)。而「八大悉地」中,有些悉地的内容和显教所说的五神通是非常相似的。例如﹕捷足、飞空、现种种身、占圆光而生神通等(注22)。
因为受到密教重视「世间悉地」的影响,而在显教的定学中强调应该修神通,这也是《难处释》中相当别致的一环。
(四)慧观偏应成
在《难处释》第九章「智慧与方便」中,阿底峡依照《中论》惯用的论证方式,以「四大因」成立一切法无生、无自性(注23),并引用《二谛经》(bden gnyis)及《智心髓集要》(Ye shes snying po kun las btus pa)等经教和论典,成立「能观的慧」在胜义上也无生、不存在(注24)。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阿底峡见依中观。不过,阿底峡评破唯识,是站在胜义的层面而立论的。如果退回到世俗的标准,是否可以允许「唯识无境」的理论成立呢﹖对于这个问题,阿底峡并没有进一步地探讨。因此,很难判定《难处释》究竟采取中观宗那一个分派的观点。不过,阿底峡自述中观宗的传承时,除了龙树、提婆以外,只提到月称、清辨、寂天和菩提贤(注25),没有提到瑜伽行中观派的代表学者──寂护、莲花戒、解脱军、狮子贤等人,只有在论说「一多正因」时,引用了寂护《中观庄严》(dbu ma rgyan)和吉祥藏(dpal sbas)《入真性注》(De kho na la‘jugpa'i grel)中的一颂。而《难处释》中所推荐的中观典籍,也没有一部是瑜伽行中观派的著作(注26)。据此大概可以推论﹕阿底峡宗于瑜伽行中观派的可能性最小。
剩下来的经部行中观派和应成中观派两派之中,到底阿底峡宗于何派﹖这个问题相当棘手。因为《难处释》中,无论在师承方面或著作方面,月称与清辨都是平行并列的。或许阿底峡认为﹕站在实证的立场来看,月称和清辨学说的微细差异并不冲突,都足以引导人证入真理,因此不严格区分二者而一并采纳。另一种可能的情形是,阿底峡重实修而轻宗义。他一再强调﹕应当修习从龙树传下来的要诀,切莫死守宗派的教义(注27)。重视实践而又不重宗派义理的人,往往会忽视宗派教义的精微处。即使发现其中有些差异,也无暇无心去细究整理。在这种情况下,不辨月称与清辨学说的细微差异而一视同仁,不是很可能吗﹖
总之,单从《难处释》的中观传承和所引的文献,我们无法分辨阿底峡的慧观思想究竟以何为宗。不过,在「智慧与方便」这一章里,有三十个颂谈到了修习中观见的要领,从这三十颂,仍可隐约看出一些宗派思想的偏向。
1、第1颂说﹕观察真实性时,宗派中所探讨的义理都是错误虚伪的。第13颂说﹕自他宗派或成立诸法为有,或成立为无,但是在究竟义名,根本不能成立有与无。第17颂说﹕修习胜义的时候,不须依靠比量的智慧。
从以上三颂来看,阿底峡主张﹕世间比量纯属虚妄,不足以成立胜义。这一点比较近于月称的观点,而别于清辨。因为清辨承认,有个世间胜义谛介于世俗谛与胜义谛之间,藉此世间胜义谛可以说明、导向真胜义谛(注28)。月称则主张﹕真理离言,虽有喻可譬,却无因可立。所以自宗不预设特定的比量,仅权巧借用敌宗为因,论破敌方,令其悟解自宗的立场(注29)。
2、讨论到胜义谛的时候,这三十颂中的第7、8、9、10等五颂的内容与月称《入中论》的说法完全一致。例如《难处释》说﹕眼翳尚未痊愈的时候,我们不能使有眼翳的病人看见没有毛发的视像。一旦眼病好了,却又不能使他看见有毛发的视像。同样地,如果无明的眼病医好了,睡梦也清醒过来了,那时,所有的一切现象,甚至于能领受的识也都完全不存在了。如《入中论》说﹕「如眩翳力所遍计,见毛发等颠倒性,净眼所见彼体性,乃是实体此亦尔。」(注30)
仅凭上述两点理由,要肯定《难处释》的中观见属于应成派,当然是不够的。充其量只能说,它比较偏向应成中观的观点,仅是而已。西藏格鲁派宗喀巴大师和其它写作「宗义书」的学者──如嘉木漾?协巴(’Jamdbyangsbzhadpa,1648~1721)和章嘉(1Cang skya,1717~1786)等人,判别阿底峡于月称应成派(注31),大概也是出于这个原因吧﹗
(五)贯通显密
阿底峡认为﹕密咒乘胜过波罗蜜多乘,是属于更上一层楼的修法。因此,说完波罗蜜多乘以后,就在《难处释》的最后一章宣说「密咒乘」──无上大乘中的最大乘。其中主要的内容是说﹕想疾速圆满福慧资粮而修学密咒法门的人,必须先承事师长,令师长欢喜。待求得灌顶和随许之后才能修习。其中,「密灌」和「慧灌」,出家众不能求受,否则不但不能获得成就,反而会犯戒而堕落三恶道(注32)。显然,在为利众生愿成佛的发心基础上,《难处释》结合了波罗蜜多乘与密咒乘,形成一部贯通显密的修道次第的论典。
印度的无上瑜伽密,兴于第八世纪前后。在此以前的大乘显教论典相当纯粹,几乎看不出有全面结合密教修行体系的趋势。第七世纪以实践著名的寂天,在他的名著《学处集要》中,也只是引用了一些真言而已,不涉及密教修法的全体。到了第九世纪达磨罗王时,兴建超戒寺,显密并弘。自此以后,密教日益兴盛。不过,一般学者写作显密论著时,大都分别处理,各成体系,很少把显、密之学贯通成一个道次第也就是﹕以菩提心贯通显密。先三归、三学﹔由戒得定,由定起通,双运智慧与方便﹔最后升进密乘,以不共修法疾速圆满福慧资粮,成就正觉。如此显密一贯的修道次第,除了《菩提道灯》与《难处释》以外,恐怕很难再找到同样性质的论著了(注33)。
(六)重视实践广引教理
一般说来,属于修道次第论著的最大特征,就是重视实践、强调修行。《难处释》正是这样一部实践意味浓厚的修道指南。其中,谆谆告诫藏人应该实修之言教,处处可见。
例如﹕
「当今之日无暇广听闻,犹如舟筏广大诸经论,是如当断一切扰意缘,唯修最胜亲承之教示。人寿苦短知识无边际,此生寿量尚且不可知,是故当如鹅饮水中乳,依信唯取所求有义事。」(注34)
「是故应当弃比量,思辨为主诸论典,应当修习圣龙树,教理传承之口诀。」(注35)
「既知牟尼正法命,出如至喉将沦亡,此时烦恼力最盛,求解脱者勿放逸。」(注36)。
「因恐文太繁,于此不广陈,仅就已成宗,为修故精说。」(注37)
「我所详述此种胜教授,乃至佛陀教法住世间,具足悲心与菩提心者,愿彼日夜精进勤修习﹗」(注38)
从上述的引文可以看出,《难处释》的确是一部为了指导人修习大乘佛法而写的论典。更加难得的是,这部修行指南有非常完整的理论架构,此点上节已经详明,兹不赘述。除了完整的理论架构以外,《难处释》更指出每一个修行阶段所应阅读大乘的经典、密续与论典,把修持和教理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综计其中所列、所引经论之数,约达150部之多,远胜寂天《学处集要》中所引的经数。又,《学处集要》中只引经续,而《菩提道灯释》则兼引论典。兹将其中所引列的经、续论典,依照西藏大藏经目录的分类,作表如次(详见拾)﹕
┌──┬──┬──┬──┬──┬──┐
│密咒│经集│宝积│般若│华严│戒律│
├──┼──┼──┼──┼──┼──┤
│45 │38 │15 │4 │2 │2 │
├──┴──┴──┴──┴──┴──┤
│甘珠尔106部 │
└─────────────────┘
┌──┬──┬───┬──┬──┐
│中观│唯识│密咒疏│毘昙│般若│
├──┼──┼───┼──┼──┤
│29 │9 │3 │2 │1 │
├──┴──┴───┴──┴──┤
│丹珠尔44部 │
└───────────────┘
从上表可以看出,《难处释》中所引佛典,有显有密,有经教有理论。经典方面,「经集」与「宝积」类偏高。论典方面,「中观」居冠。像这样强调实践而又广引教理的修道指南,自然也构成了《难处释》的另一特色。
六、《难处释》对西藏佛教的影响
观行圆备的《菩提道灯》,由阿底峡撰成并宏传出去以后,有效整顿了后弘期西藏佛教紊乱的教理与躐等的修习次第,使西藏佛教步上教理系统化与修持规范化的正轨,并逐渐兴盛起来(注39)。自此以后,西藏有关修道次第一类的论书,大都以《道灯》为蓝本。例如达波噶举派(Dwags pobka'brgud)的始祖冈波巴(sGam po po,1079~1161 A。D。),结合《道灯》与密勒日巴(Mi la ri pa,1052~1135A。D。)的「大手印」法门,《大乘菩提道次第解脱庄严宝论》,其中引用《道灯》多达14处(注40)。其次,宗喀巴的《广论》,也被认为是《道灯》的广注。因为,该论一开头就说﹕本论总依《现观庄严论》,别依《菩提道灯》(注41)。而且其中的内容,除止观方面有显著的差异外,整个理论架构大致取自《道灯》。由此可见,《道灯》对西藏佛教最大的贡献,在于提供完整修道次第的架构。
《难处释》是《道灯》的自注,《道灯》义理不明确之处,释中都有简要的说明。除了提示各项修持要领以外,释中更举出170多部相关的重要经论,为修学者指出研读经论的方向,完善地结合了理教与实践。这一点,对西藏佛教日后的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因为一个宗教是否可以历久弥新,除了外在客观的政治和经济因素以外,端赖教内的理论与实践能否紧密地结合。如果偏重理论而轻忽实践,则易形成徒托空谈,华而不实的局面。如果偏重实践而缺乏理论,则失其依据﹔容易混同流俗,盲修瞎练而自误误人。只有在解行并重的情况下,宗教才可能进一步地发展。
由于阿底峡在《难处释》中强调解行并重,进而明确地指出研读经论的方向。职是之故,他的弟子都非常重视经论的讲习﹔甚至主张﹕佛说的一切教典(bka‘)都是凡夫修行成佛的必要指南与教授(gdamg ngag),都应该学习,不能偏废。这一派的学人,便因此而获得了噶当派(bKa’damg pa)的美名(注42)。当然,对于其它各大教派,这种学风多多少少也促成了重视教典的正面影响。重视教理的萨伽派(Sa skya pa)和格鲁派,就是两个很好的例证。
此外,在戒学方面,宗喀巴的《菩萨戒品菩提正道论》(Byang chub gzhung lam),曾数处引用《难处释》增上戒学的说法(注43)。在慧学方面,《难处释》对月称中观论著的推崇,也引起西藏巴曹译师等学者的注意。在巴曹译师及其弟子长期翻译和讲习的过程中(注44),月称应成中观派的学说逐渐获得肯定与推崇,甚至因因明辩论术的提倡而获得发展,在西藏大放异彩(注45)。宗喀巴更在月称中观论著的基础上精益求精,进一步发展出独创一格的修观体系(注46)
总之,《道灯》对西藏佛教实修方面的影响非常巨大、明显,这一点一般人都看得出来。《难处释》的影响虽不明显﹔但是,其中含摄了当时印度盛传之学,更结合了实践与教理二轨。它宛如一盏暗夜明灯,为西藏佛教日后的发展提供了最正确的导向。而月称应成派的学说能在西藏获得重视与进一步的发展,《难处释》的引介更是功不可没。
七、《难处释》与《广论》之差异
宗喀巴之《广论》,依据《菩提道灯难处释》撰写而成,其理论体系之精严与完整,较《菩提道灯释》有过之而无不及,自不待言。其次,此二论著前后相距三个半世纪,于此漫长的期间,西藏佛教之实践和理论体系,应该有更进一步的发展。是以,这两部修道次第的论著,在内容上应该也有些差异。今试举其大者言之﹕
1、《难处释》详论大乘,而《广论》则通于凡小,以下士及中士之学,为上士必备之基。这是由于宗喀巴兼采《现观庄严论》,以菩萨道概括三乘之说的原故。
2、在归依、发菩提心之后,《难处释》依三学分章,而《广论》则继之以六度四摄。二者次第略有不同。
3、《难处释》论止,一本中观师菩提贤的《定资粮品》。《广论》立说,全依瑜伽学派《解深密经》与《声闻地》诸籍。
4、《难处释》第十章专论密咒乘,分析密典为七部。《广论》则略说数语便止,另辟专著《密咒道广论》(sNgagsrim chen mo),详论密咒修道次第。其中,举凡「清净菩提心」、「四类灌顶」、「守护律仪与三昧耶」、「生起次第」与「圆满次第」等五品修学次第及四部密续之说,未见于《难处释》中,大底为宗喀巴之创说。
以上所举四端,全同吕澄《西藏佛学原论》,而吕氏之书,论述尤详,可资参考(注47)。以下两点,则为《原论》未尽之处,而为本书所发明者。
5、《难处释》并举月称、清辨之论,不以为异﹔《广论》则独尊月称应成之见,以为究竟。此为二论论慧学最大之岐异处。吕氏以为﹕阿底峡之书,于瑜伽犹有所取﹔而以「为修故而说」一语成立其说(注48)。此理未见得当。盖「为修故而说」一句,系指为观修者择要而谈,与瑜伽学派无必然之关系。又,《难处释》中所述传承,未及寂护、解脱军、师子贤、莲花戒之辈﹔所举中观论典,亦鲜有彼等瑜伽行中观派之著作。是以,《原论》中「阿底峡传寂天和会中观瑜伽」之说,仍有待商榷。况且,寂天在《入菩萨行》辩破唯识,不遗余力(注49),怎能说是「和会中观瑜伽」﹖此理不辩明矣﹗
6、《难处释》论发心时,分愿、行二心。愿心由「知一切有情如母」、「欲报母恩」而生「慈」,由慈引「悲」,由悲发起「愿菩提心」。而行心体性,即菩萨律仪,为愿菩提心之增上,故称为「增上意愿(lhag bsam)。关于此点,《难处释》中引《虚空藏经》和《圣真实集法经》为证说﹕
「善男子,若由两种法摄持,则菩提心住于不退转。那两种﹖意乐和增上意乐。…增上意乐由不贪意乐和胜进修行摄。…胜进修行由福德资粮和智慧粮摄…。」
「追求殊胜功德,就是增上意乐,增上意乐就是﹕善待诸生灵,慈爱一切有情,恭敬一切圣者,悲愍诸世人,承事上师…」(注50)
由此看来,增上意愿是指﹕发起愿菩提心以后更进一步的修持功夫。它应该属于行菩提心,不属于愿菩提心。然而,《广论》中却说,阿底峡传来「修菩提心七种因果教授」,所谓「七因果者」,即愿菩提心从增上意乐生,增上意乐从悲生,悲从慈,慈从报恩、报恩从念恩﹔念恩从知母恩生(注51)。其中,将「增上意乐」置于发起愿菩提心之前,是愿心的因而非其果──行菩提心。而且,《广论》中也没有引出足以自圆其说的经论依据。更重要的是,与阿底峡相去不远的噶当派学者甲?怯喀巴(Bya。Chad kha pa,1101~1175)和曾游学噶当派门下的冈波巴,在他们的名著《七义修心法》(Blo sbyong don bdun)和《解脱庄严宝论》中,都没有提到「增上意乐」一词(注52)。
由此可见﹕发心「七因果」很可能是宗喀巴更异之说。他认为﹕希望一切有情离苦得乐的四无量心,声闻独觉也有。但是有勇气自己承担救度有情的重责大任者,则非大乘莫属。因此,便在「悲」和「愿菩提心」中间,加进「增上意乐」一项而成为七种因果。
总之,宗喀巴「七因果发菩提心」的说法,创意虽美。终非阿底峡论发心之原意。
私意以为﹕在愿菩提心之前增加「增上意乐」一项,并无必要。因为声闻独觉固然也有大悲,但是却缺乏「为利众生愿成佛」的意愿,因此可以用有无「愿心」来判别大小乘,不必在「大悲心」上硬作区分,别出「增上意乐」一项。「增上意乐」,应该是「愿心」增强到某种程度以后,自愿为利益众生而受持菩萨戒,学菩萨行的「行菩提心」。
(注1)Jaschke,Tibetan Grammar中,允许此种语法的存在(New York,1966,P。59)。
(注2)参见《阿底峡与菩提道灯释》中,《菩提道灯》,第67颂。
(注3)参见《菩提道次第广论》。台北﹕文殊出版社,民国六十七年。以下简称《广论》。页239~40。
(注4)同(注3)。另见(注2)引书,页109。
(注5)同(注3)。
(注6)参见《广论》,页4。
(注7)见吕澄着,《西藏佛学原论》。台北﹕老古出版社,民国六十七年,页72。
(注8)见《阿底峡尊者传》。台北﹕佛教出版社,民国七十五年。「附录」,页88。另见《望月大辞典》,册1,页40b。
(注9)见(注2)引书,页84。
(注10)见大正,30,642中。
(注11)参见圣严着《戒律学纲要》。台北﹕东初出版社,民国七十七年,页38。
(注12)参见(注2)引书,页96。
(注13)参见(注2)引书,页98。
(注14)参见(注2)引书,页142。
(注15)参见(注2)引书,页171。
(注16)参见(注2)引书,页172~175。
(注17)参见(注2)引书,页181。
(注18)参见(注2)引书,页191。
(注19)参见(注2)引书,《菩提道灯》,第35、36颂。
(注20)参见(注2)引书,页194。
(注21)参见(注2)引书,页246。
(注22)参见(注2)引书,页247。
(注23)参见(注2)引书,页209。
(注24)参见(注2)引书,页217。
(注25)参见(注2)引书,页213。此中的清辨,也可能是《中观宝灯》的作者──另一较后出的清辨(参见江岛惠教,「阿底峡的二真理说」,《龙树教学的研究》。东京﹕春秋社,1979,页389以下)。
(注26)参见(注2)引书,页214。
(注27)有的日本学者认为﹕阿底峡的《中观要诀开宝箧》中,夹杂着瑜伽行中观派的思想(《西藏佛教史》,页118)。
(注28)参见野泽静澄「中观两学派的对立及其真理观」,收入《中观与空义》世界佛学名著译丛,册62,民国七十五年,页153~4。
(注29)同注28引书,页163~5。
(注30)见月称着,《入中论》。台北﹕新文丰出版社,民国六十四年,卷2,页19。
(注31)参见《广论》,页408﹔Hopkins,J。,Meditationon Emptiness。Wisdom Publication,London,1983。P。432,534。Lopez Donald Sewell,Jr。,The Svatantrika-,MadyamakaTenetSystem,University Microfilms Internation,Michigan,1982。P。387。
(注32)参见(注2)引书,页256。
(注33)阿底峡另一部著作《定资粮品》(Ot。5398),也结合了密咒乘的修定法门(参见《广论》引文,页72)。
(注34)参见(注2)引书,页256。
(注35)参见(注2)引书,页215。
(注36)参见(注2)引书,页220。
(注37)参见(注2)引书,页261。
(注38)参见(注2)引书,页261。
(注39)参见王辅仁着,《西藏密宗史略》。台北﹕佛教出版社翻印,民国七十四年,页67。
(注40)参见冈布巴着,《冈波巴大师全集选译》。台北﹕法尔出版社,民国七十六年,页125~363。另见《西藏佛学原论》,页38。
(注41)详见下文。
(注42)参见王森着,《西藏佛教发展史略》。北京﹕中国社科出版社,1987,页51。
(注43)参见宗喀巴着,《菩萨戒品释》(收入《大藏经补篇》,册8)。台北﹕弥勒出版社,民国七十五年,页703、705、727、751。
(注44)前文已详。
(注45)西藏的因明学,十一世纪后半,开始受到重视,以拉萨南郊的桑浦寺(gSang phu)为中心,翻译、注疏、讲说因明论典。到十二世纪中叶,甚至发展出一套独特的辩论模式(参见《西藏密宗史略》,页97~8)。而此辩论术的产生必然有助于中观应成派学说的进一步发展。
(注46)参见《西藏佛学原论》,页71~89。
(注47)参见《广论》,卷17~24。另见法尊撰,「宗喀巴大师的菩提道次第论」,《广论》(页12~15)。
(注48)参见《西藏佛学原论》,页86。
(注49)参见《入菩萨行》,「智慧品」第26~29颂。
(注50)以上参见本书,第四章。
(注51)参见《广论》,页225。
(注52)参见《冈波巴大师全集选译》,页189~239。《大乘修心七义论释》,台北﹕新文丰出版社,民国七十六年。页89~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