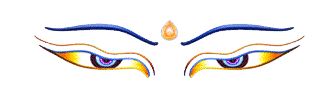西禅寺在湖南省衡阳县,本文传主观空法师是湖南耒阳人,与衡阳邻近,所以青年时期投入衡阳西禅寺出家。但为时未几,就到南岳上封寺受戒,继而参学各地,行踪不定,所以他在西禅寺停留的时间并不长久,甚至於以後也未再回去过。但他毕竟是在西禅寺落发出家的,所以我们称他为衡阳西禅寺释观空。他是太虚大师门下的学问僧,也是近代中国佛教中有名的学者。
观空法师俗家姓廖,湖南省耒阳县人,清光绪二十九年(一九○三年)出生。他少年好学,就读私塾,受儒家传统教育。民国八年(一九一九年)十六岁的时候,投入衡阳西禅寺,礼智玄长老座下披剃出家;同年到南岳上封寺受具足戒。先是空也法师在南岳讲经,民国八年(一九一九年),应长沙开福寺之请,在开福寺创办佛学讲习所。观空於受戒之後,正赶上讲习所开课,乃到长沙请求入学,从空也法师学经教。由於他在讲习所中年纪最小,天资颖悟,功课每列前茅,所以深为空也法师所青睐。
民国十一年(一九二二年),太虚大师在武昌创办「武昌佛学院」,请空也法师到武院任教,观空随著空也法师到了武昌,进入佛学院第一届肄业。武昌佛学院的学制,原定为三年毕业,後来太虚大师以学生人数过多(武院第一期,学生最多时超过百人),程度参差不齐,乃把第三年的课程合并入第二年上完,打算提前於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年)璁假毕业,另行招生。但还没有到璁假,在日本学习东密,获有阿 黎位的大勇法师,回国到了武汉,建坛传授密教,於是武汉三镇掀起了一阵学密的热潮。大勇於一个多月中开灌顶坛十次,入坛学法者除社会上的男女居士外,武昌佛学院的在校学生及职员,也有多人依大勇学习密教。
不久之後,大勇到了北京,他想率领一批学生到西藏去学密教,乃先在北京慈恩寺成立了「藏文学院」,为入藏学法做准备。武昌佛学院的职员学生中,有十多个人到北京入藏文学院学习,观空也在内。一年之後,大勇把藏文学院改组为「留藏学法团」,准备率团赴西藏。民国十四年(一九二五年)秋,在胡子笏、汤铸新等护法居士的经费资助下,大勇率领著观空、法尊、大刚、法舫、严定、会中等二十馀人,自北京出发,经汉口、宜昌,乘轮溯江而上抵达四川。入川後首抵重庆,继到成都,於朝礼峨嵋山後,继续向西藏前进,於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年)十月,抵达西康康定县(著名「打炉」)。这时西藏当局怀疑学法团有政治目的,多方阻挠,不允入藏,学法团不得已暂留康定。时团员中各人藏文程度参差不齐。既然不能前进,即同往跑马山,依止降巴格西学习藏文,及听格西讲《比丘戒》、《菩萨戒》、《菩提道次第》等密教经典。他们预定次春入藏。一行人共同发下大愿∶「赴藏求法,乃吾侪之志愿,环境愈困难,意志愈坚定,纵令纷身碎骨,尚期来生满愿,何况其他乎?」
到了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年),蹉跎到秋天,大勇率领学法团继续前进,行至藏边甘孜地方,又为当地驻军所阻,不得已遂停留在甘孜。为不虚渡光阴,一行人依札迦大喇嘛学习藏文及密教经典。这时国内正当国民革命军北伐时期,政局丕变,原先支持学法团经费的一些大居士也受到冲击,这就影响到学法团的经费来源。同时藏边地区,气候酷寒,团员多数不能适应,亦有水土不服者,以致相继病亡,年馀之後,健存者已不到二十个人。到了民国十八年(一九二九年)秋,团长大勇法师也积劳成疾而逝世了。法尊、观空等给大勇料理完後事後,仍继续留在甘孜学习。原来的一行人中,除病死逝之外,法舫感於入藏机缘未熟,返回武昌佛学院去了。此时出家众还剩下法尊、观空、大刚、严定、恒演、密严、密悟、密慧、密字、慧深等上十个人。到了民国二十年(一九三一年)春,法尊与慧深往昌都亲近安东格西学法,半年之後恒演、密悟也前进入藏。此时太虚大师在重庆北碚的缟云寺,创办了「汉藏教理院」,有函相召,要法尊、观空、严定、超一等回重庆去。四人以大师之召,不可违拒,乃摒档行装,由甘孜返回四川。
观空一行人回到重庆後,太虚大师命他们三人到汉藏教理院,法尊以教务主任代理院务,观空、严定在院任教,超一担任庶务主任,严定後来也兼任了藏文系主任。观空在教理院任教多年,到民国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年),应聘到北京讲经。他自感先前在西康数年,未能进入西藏,深引为憾,乃决心二度再赴西藏,学习密法。他在北京讲经完毕,即自天津乘船到上海。由上海再乘轮船经南洋转赴印度,在印度朝礼圣迹後,由印度进入西藏。
当时入藏有两条路,一条是由四川经西康入藏,行程要三、四个月,中途艰险万状;另一条是由印度入藏,行程较短,只需三、四十天,但艰险尤有过之。因为这条路途中山高入云,雪深没胫,没有旅舍饭店,找到山居人家,於牛房马厩中过夜,以地为床,以牛马粪为席。山中水贵如金,无水盥洗,蓬首垢面,不似人形。观空在途中历时月馀,受尽艰苦,终於抵达拉萨。
观空到拉萨後,住入哲蚌寺,依康萨仁波切、颇章喀大师、噶登巴喇嘛等,学习密教经典,先後受多种灌顶承法。哲蚌寺是西藏最大寺院之一,与布达拉宫、大昭寺合称三大寺。哲蚌寺在拉萨之西六公里处,是黄帽派(黄教)的寺院。建於西元一四一七年,由宗喀巴的大弟子甲养曲吉奉师命所造,是喇嘛寺中最具威望且僧侣最多者。内地僧侣入藏学法者,多住在哲蚌寺。如能海法师二度入藏,与弟子多人均住在此寺。康萨仁波切是西藏年高德劭的大喇嘛之一,能海法师也是依康公学法的。
观空法师在拉萨哲蚌寺修学了十年,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九五○年解放军入藏。当时拉萨兼通汉藏语的人才极端缺乏,解放军人员乃聘请观空到西藏日报社,担任编译的工作。观空於工作之暇,把藏语中的名词、术语等,加以整理、汉译、编印成册,这对学习藏文的人提供了方便。一九五七年,北京的中国佛教协会,知道了观空在藏传佛教的造诣,乃把他调到北京,安置在位於北京法源寺的中国佛学院担任教职。两年之後,在佛学院研究部担任指导教授。由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六六年,前後十年之间,他指导学僧把藏文的《中论文句》、《四百论》、《中观自续派》、《中观应成派》、《宝鬟论》、《六十顺正理论》等中观一系的主要论著,翻译为汉文,他亲自加以修改订正,弥补了汉文论著中此系文献的不足。
一九六六年夏天,文化大革命开始。在「十年动乱」期间,出家人都受到了斗争,连中国佛教协会创会元老巨赞法师也被捕系狱;及具有全国政协特邀代表、佛教协会副会长等头衔的能海法师,也在五台山受到批斗,因而逝世。所以观空自也难置身事外。他受斗争的详情如何,不得而知。一九八○年後改革开放,观空老法师此时已年近八旬,重新露面参加佛教活动,他在中国佛教协会从事藏文经典的翻译工作,并将早先被译为藏文的唐代圆测法师所著的《解深密经疏》的後六卷,还译为汉文。
数年之後,观空老法师八十多岁了,健康日渐衰退。一九八九年春,老法师到福建莆田广化寺静养,同年七月五日在广化寺示寂,世寿八十七岁,僧腊七十一年。
观空老法师少年出家,前半生一直努力刻苦学法,後半生则译经教学,一生生活艰困清苦。而他生性恬静,澹泊自守,不事攀缘,不慕虚荣。他治学严谨,教学认真,立身严以律已,宽以待人,韬光养晦,不炫才华。他的译作除前所述及者外,尚有《木喀日巴略传》、《缘起赞句略解·见深义眼》,及多种仪规、愿文等。又曾摘译《三主要道讲录·开妙道文》和《妙吉祥最胜赞》等。 |
 发表于 2006-11-22 22:45
发表于 2006-11-22 22:45
 发表于 2006-11-22 22:45
发表于 2006-11-22 22: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