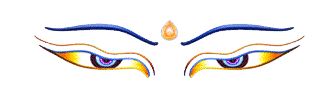我曾经是个表面看起来温和、随顺,其实内心孤傲、倔强的人。从小就习惯于冷眼看世间,觉得周遭的亲友,包括自己在内,不是受礼教约束,就是喜欢作茧自缚,活得好辛苦! 也曾尝试着在书本或宗教上寻求心灵的解脱,但总不得其门而入。而看到有些人虽口说修行,却割舍不下情爱,更让我不免感叹,为什么事到如今还看不清楚,只要是还没有醒来,那么就算是再恩爱的夫妻,到头来黄泉路上亦俩不相识! 于是我一意孤执地把自己摒弃于人外,不信任亲情、爱情、与友情,总在紧要关口,牢牢守住那最后一道关卡,不让任何人轻易闯入我内心的世界。
十几年前父亲病逝以后,更让我对这个人生缺乏眷恋。虽然父亲在世时,我们父女俩根本就缺乏心灵的沟通,我年少时甚至叛逆到令他气得想要和我断绝父女关系,但我心知肚明,任何时候只要我倦了,他都会张开双臂,接纳我回家休息、疗伤。父亲这一走,等于断绝了我在这世俗上唯一的依靠,虽然母亲与弟妹依然建在,我也有个属于自己的家庭,但心灵上我却再也无「家」可归了。随着父亲的辞世,我内心深处也经历了一次死亡的风暴。那时,我的想法是,既然此生注定孤寂,最起码我得像大鹏鸟一般,在内心的世界里自由地展翅飞翔。
老师的出现,却像阳春溶雪般地使我已冰冷的身心逐渐温暖、复苏。
第一次见到老师,他就强调修行中的无为,提到在修行这条路上,除了「看」以外,其实我们什么也做不了。当时,我就有一种奇特的感觉,好像等了好久,就是等着这个人出现,以肯定的口吻,把隐约藏在我潜意识层面上的某种认同,挑明讲了出来。不久,他又带着我们读莲花生大士所作的「无染觉性直观自行解脱之道」,要我们了解其实内在身心的各种境相,无非是自性的自然展现,它当下升起,也当下自行寂灭解脱。我们只须安住当下心境,顺其自然,不修整造作地纯然观照就行了。
那时,我心中又是一阵震憾,感到长久以来在黑暗中这么独自摸索、寻觅,到此刻才得见一线曙光。我那时对老师其实一无所知,但这并不重要,我只知道他讲的话有很强的穿透力,直接打进我心坎。而他所散发出来的那股亲切感,也让我感到在人生这条路上,原来我并没有像自己想象中那么孤单。于是,我直觉地认定他就是来引导我修行的师父,而「纯然地看」,也从此成为我修行的口诀。
但在理念上接受和心灵上产生共鸣是一回事,怎样才是「纯然地看」呢? 老师又说了,除非头脑停止运作。而要使头脑停止,就必须去走路,但走路时要轻松,如实地看着自己身心的变化,就算被念头带跑了,知道就好,无须谴责,再度让觉知回到脚底。
就这么简单吗? 头脑停止又会是什么状态呢? 当时心中虽然纳闷,但我还是去走路了。
起初在户外走路时,总是不得要领。不是注意力被沿途的虫声、鸟语或自然景致所吸引,就是忙着心内的独白,往往要在走路四、五十分钟以后,这心才会收敛一点。但我从小就有「愚公移山」的精神,做任何事只管一切尽其在我。于是再度揣摩着老师提示的要点,走路时开始能逐渐轻松自在地感觉脚底,同时看着自己皮肤毛孔的张合与呼吸的变化。
我就这么一步、一步地走着……. 起初只是每天下班回家后,抽出一段时间去走路。到后来,这习惯也延伸到日常生活中。任何时地,都把握机会,觉知脚底,看着自己身心的变化起伏。就这样,我的觉知先是一点、一点增加,再连成一线,然后逐渐成片,到后来则是绵绵、密密。随着觉知层面的扩展,量变产生质变,一些事情开始发生了。在走路当中,我会和路边自然的景物连结在一起,感觉周遭的蝉鸣、虫语声似乎是从自己体内发出。
偶尔,在黑暗的夜晚走路,在心很宁静时,我会看到自己手背上的肌肤居然透出晶莹的光彩。有时,走着、走着,这个在走路的我似乎消失了,只剩下一双脚在那儿迈步前进。原先必须刻意去维持的觉知,竟自然启动。我的身心开始产生蜕变。
首先,由于人轻松了,愈发看清楚在人生这场梦中,自己只不过是一再轮回地扮演各种不同的角色罢了,既然是在演戏,又何必那么自苦呢! 于是在工作上的态度有了显著的转变,再也不那么自虐似地凡事往身上揽,并处处要求完美。也逐渐能用欣赏的眼光看到他人的优点,而把手边很多的事务能放则放,把功劳推出去。正因为心理少了一些不必要的纠葛,我与上司讲起话来愈发直接、勇敢,看在同事眼里,都很讶异,为什么我这个东方小女子竟敢「犯上」,而上司却依然倚重于我。而在婆媳关系上,由于我心境日趋宁静,应对中较少夹杂着负面的情绪或过往的恩怨情结,婆婆和我之间近几年竟变得像能谈心的朋友。
其次,我发现身体内在的能量正日渐增强,感觉的触角变得出奇地敏锐。在没有预期的状况下,一个内呼吸已自然地在体内形成,造成气动,在我全身上下流转,使我对自己的身体,包括体内水、火、风的运作,逐渐有了更细腻的体会与认识。我开始能听到血液在我血管里流动的声响,有时似小溪低语,有时在穿过大腿部位时,竟又如滚滚波涛。生理上的一些病痛于兹逐渐被调整过来。
而随着走路时日的增加,我更在不期然中走进一个广大而超越时空的天地里。我开始能感知一些非头脑思维所能理解的讯息,一些奇妙的现象也跟着出现,尤其是在每回和老师接触以后,这些现象发生得更是频繁。有时,闭眼想静坐一下,不是突然置身在一片光中,就是像观赏电影般,看到一些往日从未见过的山川景色和人物画面,在面前一格格放映。有时听音乐时,也能感知、看到那首曲子的色彩! 我开始作一些有关修行的梦,而老师往往在这些梦里出现。
而在走路时、静坐中,一些非今生记忆的浮光掠影会在眼前闪现,某种熟悉的感觉会蓦然袭上心头,使我觉得时空易位。许多夜里,半梦半醒间,会察觉到有另一个「看」,在看着这个正在观察自己身心变化的我。起初,我对这些现象的发生很惊讶,但秉持着老师对「纯然地看」所定下的原则,于是就只是看着它们,它们也随之消逝。偶尔想到了,就打电话向老师报告一下发生的现象,而他的反应总是那么的惜言如金:「嗯,很好,继续看。」久而久之,我也就养成凡事继续看下去的习惯。直到几年以后,我才从他那儿又学到一个新的名词,叫做「无作妙力」,才知道原来这些现象会发生,是因为我长期走路,观察身心,而使自性的「无作妙力」自行展现。
但更奇妙的是,当我逐步地走入自己内在的身心世界时,我和老师之间的互动也产生了微妙的变化。由于客观因素,他的禅修班我参加的次数寥寥无几,更别提到德州长期追随在他身边。因此在相识的这几年里,师徒之间的接触,主要还是靠着电话连系,或是他每年来美东探视学生时,和我们短短几日的聚首。所以我格外珍惜能和他相处在一起的每一分、每一秒。而每回的接触,虽然时间短暂,事后我都会发觉自己的身心在不期然中已被催化,变得更松软,使我对他充满了惊叹号。
正因如此,起初看到同修们能去德州参班,或陪着他出游,心中好生羡慕,觉得他们真幸运,相对地落寞的情绪不禁产生。也曾质疑自己能否够做老师的学生,不然为什么他频频召唤,我却总是不得成行? 但这种疑问持续不久就消逝了。我对自己作下期许,既然不能长随左右,就不妨照他教的,好好去走路吧,如果有缘,我们自然会再相见。
就是这种心境的转折,使走路更成了与我生命攸关的一部份,使我因之得以逐渐成长,学到了师徒关系这一门重要的功课。回首过去几年,我才发现,经由走路,我和老师之间的师徒关系,已经历了几个阶段:
在认识老师初期,我对他的感觉就像是遇到了久别重逢的亲人,有很深的倚赖,总是一厢情愿地认定他会永远在那儿指导我,做我的师父。记得相识一年多后,有一回和他通电话,他提到即将百日闭关,要停止每周的电话连线上课时,我当场就差点掉泪,这才意识到自己原来脆弱的像个长不大的孩子,对他的依赖竟有这么深。后来想尽办法,在老板及先生那儿讨价还价,赖出四、五天时间,准备飞往德州见他时,预定要搭的班机却临时停飞,耽搁了三个多钟头才起程,让我急得在费城机场的候机室里来回踱步了好一阵子,这心才定了下来。
那趟德州之行,与老师同处在一个屋檐下生活几天,不仅让我对他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也使我在修行上有了重要的突破。多年来静坐或念佛都无法让心不向外攀缘,却在某一夜老师巧妙的引领及平日走路打好的基础上,使我从此不再轻易为外尘所转。打从那时开始,我对老师由衷的折服了,对他的敬爱也与日俱增。
但我却是抱着逃跑的心态离开德州的。
人真是很矛盾的动物,一方面我直觉地认定老师是师父,视他为至亲之人,另一方面又很惶恐,深怕再度失落,尤其是想起自己几年之内实在无法经常跟随着他。而心情落寞的时候,头脑的介入,使我又惯性地竖起那道心防,想逃离老师。我这个徒弟竟不敢把自己交托给师父,让他再踏进我内心深处一步! 看到自己这种患得患失的心态,我更决心要好好去走路。很多个夜晚,当同修们在德州参班时,我也在月色下踽踽独行。
走着、走着,我的脚步越迈越踏实,心也越来越宁静。我开始不再介怀自己能否去德州参班,因为终于明白,我本就是他的学生,这不是时空的阻隔所能改变的事实。我唯一能做的,就是随时把自己准备好,等候老师出现。而令我感动的,是在我还自觉是个丑小鸭时,老师却似乎比我这个徒弟还更了解自己的潜质,总用看天鹅的眼光待我,使我身心日趋柔软、层层开展,逐渐懂得要珍爱自己。在他这位师父眼中,我们这票学生,大概就像是随时会破茧而出,翩然起舞的彩蝶吧! 更感激他的,是他对我从不多用言教,既给我足够的空间让我自行成长,却又不离不弃,总是在我需要时适时出现,三言两语,就把已走偏的我,从修行的误区中带回来,让我对他讲的观照,有更进一层的领会。犹记得有一年原以为他不会来东岸了,心中已够难过,他在电话里却又旧事重提,要我去德州,被逼急了,理直气壮地抛回一句:「既然学生不能去,为什么老师不能来! 」没想到不久,他和师母真的出现。见面没讲两句话,就瞪眼直骂我厉害。我知道他其实也很开心,心想,随你骂吧,骂什么都无所谓,只要人来了就好。
就是这些温馨的点滴,无言的潜移默化,使我终于撤下最后那道心防。有一个秋夜,当我在住家附近走到夜深人静时,抬眼望向广阔的天空,看到那些在眨眼的星星,突然,我好想笑! 我懂了! 我知道了! 我发现老师其实真像是个顽皮的孩子,竟然对我开了这么有趣的玩笑! 原来时空从来不是问题,师父是无所不在的,他一直在我身边,从来没离开过。就像阳光从来不分别的把温暖散发至每一个能照到的角落,师父也一直无私地、不间断地对我们传送他的光和热。是头脑的杂音,及这颗偏执的心障碍了我,使我以往没看清楚这点。
断疑生信啊! 从此以后,在行、住、坐、卧中,只要心够静,我会在自己的每一个呼吸与脉动中感受到老师。后来在不经意间,我又觉察到,虽然过去这几年来没再踏足过德州,听老师亲口授课的次数也少,但我什么也没欠缺,可说是和经常去参班的同修们一起同步成长。好像远隔千里,我仍是能源源不绝地感受到从老师那里传来的讯息。然后,一个奇迹发生了! 当他再度来东岸授课时,我发现往往他尚未开口,他要讲的话已在我心里流过。那时老师对我而言,既是严师,亦是好友。
一年前,我的身体又有新的变化产生,原来在全身上下流动的气机更深入体内,似乎有一股能量正蓄势待发,延着一条条轨迹,遵循着圆周的次序,开始要从我右脚底往上窜,通过臀骨,贯穿腰背,直通头顶,然后向下,再次轮转。这个现象使我生理很不舒适,尤其是十一岁那年曾经摔伤并骨折的右腿。起初,只是脚底气胀,气走到脚底或腿里某些部位时会奇痒无比。然后,肌肉会抽筋痉挛。到后来则是感到痛,而这痛是深入骨髓的,让我觉得腿快要被错骨分筋了。开始时,这种情况只是每天在某几个时辰发作,到后来则演变得愈来愈频繁。往往夜深了,想阖眼休息一下,这气动又将我唤醒,逼我看着右腿的疼痛与不适。我竟必须时刻与这不适为伍! 短期之间,我体重急遽下降,身型竟回到大学时代清瘦的模样。虽还不至骨肉嶙峋,但看在周遭亲朋眼里,因为不明究理,总不免担心,认为我病了。有位朋友甚至以为我得了绝症,婉转地向我推荐医生。他们善意的关怀,对长夜无眠而不想被打扰的我,造成一种压力,也曾因此怀疑自己是否正步上父亲的后尘,将死于血液疾病。
最后决定打电话给老师,要他明确地告诉我,是否我有病。他简单的一句:「你很正常,没毛病」,使我顿时心定下来,不再理睬周遭人异样的眼光与说法,继续看着这痛。现在,我终于熬过这段疼痛期,身体又好像被清洗、调整了一番。这段过程,让我看到身体其实比头脑有智慧,也从中学到向自性臣服。
二零零五年年底,我飞往德州参加莲花湖禅堂启用典礼,也终于得偿宿愿,第一回正式参加老师举办的禅修班。那几日,以旁观者的角度默默观察,看到已有不少年轻的朋友认真地跟随着他学习走路观照,有几位还走得相当深入,感动之情油然而生,谁说曲高就一定和寡呢! 临别前夕,午夜后和几位同修至老师家辞行。其间,他没和我讲过几句话,我大多时也保持着静默,观照着自己的身心。道别时,夜更深沉,他把我们送到门外,站在那儿,亲自看着我们上车,然后车子驶去。坐在车后座,我却再没有回头望向车窗后他站在那儿的身影。
从小我就怕聚,总是怕不堪承受那聚后又散的满怀离情。而以往每回和老师分别,我也总是依依不舍。但那一夜,我的心却出奇地平静。我依然关心、敬爱着老师,但随着我愈走进内心深处,贴近自性时,那层内与外的界限被突破了。我终于明白,我们本是一体,而有种爱,是会因为变得更深更广而显得很淡。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难怪乎每回听到这句唱颂,我心内就算有再大的风浪,也会乍然止息。
老师曾说他讲的话在我身上都会成真。诚哉是言! 对我,他似乎总是有点石成金的能力,使我化成莲花,层层展开那一片片晶莹的花瓣。当他提到佛足千辐轮时,我就会觉得金色的阳光正从足底升起,照亮我整个身心。第一次在课堂上接触到他写的「紫气东来」前几段文字后没多久,我静坐在莲花湖那禅堂里,内视中竟看到漫天的紫气扑面而来,全身震动,耳际乍然一阵春雷闷响,不久一阵清凉就从头顶洒下。
别认真地质疑我这是真是假,也不要以法为实地告诉我这一切都是幻。在这戏梦人生里,探讨孰真孰假,说什么是梦是幻,又有何意义呢? 师徒之间本就是一个「诚信」罢了。其实这么说还是多余的,如果还不明白,那就再好好地去走路,轻松自在地和自己在一起吧! 当你照料好自己时,你也照顾到整个存在。
感谢一切,让我今生能遇到老师,跟随他走路。 |
 发表于 2008-3-14 23:55
发表于 2008-3-14 23:55
 发表于 2009-1-20 18:48
发表于 2009-1-20 18:48
 发表于 2010-6-25 17:47
发表于 2010-6-25 17:47
 发表于 2008-3-14 23:55
发表于 2008-3-14 23:55
 发表于 2009-1-20 18:48
发表于 2009-1-20 18:48
 发表于 2010-6-25 17:47
发表于 2010-6-25 17: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