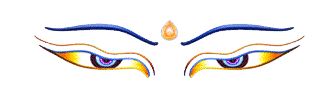大师法名袾宏,字佛慧,号莲池。莲池二字,正表明了大师的平生志愿。
大师俗家姓沈,是杭州仁和人,世代都是名门望族。大师父亲名德鉴,号明斋先生,母亲周氏。大师从小就异常聪颖,而且对世间繁华十分淡泊。
17岁那年,大师考中秀才,入县学读书,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品学兼优,名重一时,自觉考举人,中进士,犹如捡石头一样容易。当时大师邻居有个老婆婆,每日念佛数千,大师问她为什么,她回答说:「我死去的丈夫持佛名号,临终无病,与人拱手作揖就走了,故而知道念佛功德不可思议。」大师听后,从此归心于净土,自书「生死事大」四个字,贴在案角床头。且家中戒 杀生,祭祀祖先都用素食。
大师元配夫人张氏,生下一子后,子母相继而死。大师本无意续娶,但因母命难违,只得又与汤氏议婚。汤氏本是贫家女,而且长期吃素。有一个富贵人家,想要大师作女婿,就暗地里散布谣言,说汤氏的坏话。哪知大师听到后,反而立即成婚。大师的本意,只是为了能够有个名义夫妻罢了。
大师27岁那年,父亲去世。31岁那年,母亲去世。大师哭泣著说:「父母之恩,无量无边。现在正应该是我报恩的时候啊!」从这时起,大师就有了出家之心。
明朝嘉庆乙丑年除夕那天,大师让汤氏沏茶,茶杯刚放进茶盘里就裂开了。大师笑着说:「因缘没有不散的道理。」初三早上,大师和汤氏诀别,说:「恩爱无常,生死谁也替不得谁。我走啦,你自己决定自己的事吧。」汤氏回答说:「夫君先走,我随后出家。」于是大师作《七笔勾词》,投归性天理和尚削发,不久又从昭庆寺无尘玉律师受具足戒。住了几天之后,大师即独自一人游历四方,遍参善知识。
游五台山时,大师感应文殊菩萨放光。入京师,大师参访遍融、笑岩二位大德,在他们的开示中,受益非浅。离开京师走到东昌时,大师忽然有所开悟,作偈如下:「二十年前事可疑,三千里外遇何奇,焚香掷戟浑如梦,魔佛空争是与非。」
大师因母亲丧服未满,故而怀抱母亲灵骨遍游四方,凡就餐即供养,凡住宿必奉敬,哀思如此深重。当走到南京瓦官寺时,大师一病几死。正欲举火荼毗时,大师微微地说了一句:「我还有一口气」,方才停止。病好之后,大师南归越地(即浙江东部),曾经五次参加坐禅法会,始终也不知左右邻僧的法名。
隆庆辛未年间,大师乞食梵村,见云栖这个地方山水幽寂,产生了终老于此的志愿。此山本是已故高僧伏虎禅师所居寺庙遗址。居士杨国柱、陈如玉等,为大师建造茅屋三间以避风雨。大师独自一人,住于寒山岩岭。曾绝食七日,跌坐于岩壁之下。
云栖一带多有老虎为患,环山40里内,每年都要伤害数十人,居民苦不堪言。大师发大慈悲心,诵经施食,虎患竟从此绝迹。
有一年大旱,村民乞求大师祷雨。大师笑着说:「我只知念佛,没有什么法术。」众人坚请不已,大师不得已出山,手击木鱼,绕农田念佛。足迹所至之处,大雨随注。村民惊喜万分,争相出资、出工、出木材,为大师造屋。在下地基时,挖出了原来寺庙的立柱基石。大家说:「这是旧云栖寺的。大师福佑我们全村,我们愿使云栖寺焕然一新,让福佑代代相传。」新的寺院不几天就建成了,只是外边没有山门,中间没有大殿,惟有禅堂里住着和尚,法堂上供奉著经像而已,所有一切建筑,都不过是遮风蔽雨罢了。
从此以后,净土法门大兴于世,四海之内的出家人日就归附。云栖寺也就逐步成了一方大丛林。大师悲悯末法时代,佛陀教育残缺不全,禅宗道理难明,众生业深垢重,将佛陀上等醍醐,贮存于污秽器皿之中,甚可怖畏!为众生得度,佛设立三绝学(戒定慧),三学之中,戒为基础,基础不立,定慧二学何所依从?修正思维言行,必须先加固根本,而目前大江南北,戒坛已久禁不行了。为了重振颓毁的纲领,大师带领大众,依佛制,每半月诵《梵网戒经》及比丘诸戒品,远近衲子听说后,尽来归附。大师以精严律制为第一行,曾手著《沙弥要略》、《具戒便蒙》、《梵网经疏发隐》三书,以发明戒律的要旨。
大师因自己从参究念佛而得大益,故而广开净土一门,普摄上中下三根众生,极力主张执持名号,痛斥狂禅,手著《弥陀疏钞》10余万言,融会事理,指归唯心。世人都以为大师只弘扬净土,而不知这是末法中的普光明藏。
万历戊子年间,瘟疫流行,每日病死的超过千人。太守余良枢请大师赴灵芝寺祈祷,瘟疫果然顿止。
梵村原有一座朱桥,但被潮汐冲塌了,行路之人很不方便。太守请大师倡导重造。大师说:「若让我领头重造,无论贫富贵贱,每人只许布施银钱八分。」八卦之中,坤卦第八,坤属土,土能制水,这是大师用八的含义,有人说:「工程浩大,只布施八分银钱,太少了,恐怕难以完工。」大师说:「心力多,则自成不朽之功,用不了几天即可积累至千金。」施工时,每打一椿,大师都带领大众持咒100遍,因而潮汐有好几天不来,大桥也竟而因此造成了。昔日钱王建大桥时,用万人弩射,以至潮水回头。今日大师却以一心之力当之,是什么法术啊?!
大师道德日高,十方衲子日日投归,大师一如继往以慈心接待。弟子与日渐增,居住也日益狭隘。大师都本着不图好看但求实用的原则,造屋而居。大师所定清规,比他人分外恭敬。大众清修,有通用的念佛堂;若是精进的、老病的等等,则别立小佛堂。每堂各有管事,各有锁钥,定时开闭。也各有警语策句,定期宣读。夜里都有巡逻,击板念佛,声音在山谷中回荡,使修行困倦的人从睡眠中清醒,使需要卧床休息的人安心入睡。布萨羯磨,纠举功过,兴行赏罚,凛然犹如冰霜。即使是佛陀如来,在祗桓精舍时,尚且有六群比丘不守清规,扰乱大众;在大师门下众僧之中,竟然没有一人敢诤竞犯律。并未搬照《百丈清规》,而足以救济时弊,古今丛林,没有像这样的。大师所定的僧规寺约,警语策句,就是这样光明绚亮。
大师极意禁戒杀生,推崇放生。他的著作久行于世,四海之内多奉读尊敬。大师曾在净慈寺开讲《圆觉经》,每天前来听经的人有好几千,四面八方全是人墙。大师曾赎买寺前万工池作为放生池,并在他八十诞辰之际,又增广扩大。在府城中设立上方、长寿两个放生池,每年需支出银钱一百余金。在山中设立放生所,专门救赎、放养飞禽走兽,费用全从僧人口中节减,每年约需二百石粮食。各放生池所,都设有专门守卫,并定期宣示佛法。即使那些喜欢鸣叫的鸟类,闻木鱼声声,也都鸦雀无声,寂然而听。等到宣示结束,便一齐鼓动翅膀、上下喧鸣,这岂不是生物的佛性吗?是啊!佛说孝名为戒,儒家批评佛子只有养育没有恭敬。大师对于生物既养育又恭敬,而且又有礼节,难道不是孝吗?
大师道风传播日广,海内贤人豪士,无论在朝在野,无不归心感化。如兵部尚书宋应昌,吏部尚书陆光祖,内宫宣谕张元忭。再如司成冯梦祯、陶望全等,上门请法的超过百人。他们都是专程前来探求人生大事,闻法之后,无不心服口服,成为大师的入门弟子。临司守相,大小官员,一下车来就伏地拜谒。以及贤人豪杰,排队等候参见的,全都一视同仁。不多一礼,不另招待,都是粗粮淡饭分外香、草蓆漏榻自情愿。听任蜥蝎从身上爬过,蚊虫叮咬,面色如常,忘却形骸,忘却权势,倾囊供养。不是大师精诚所感,又怎能这样呢?
侍郎王宗沐问大师:「夜来老鼠唧唧,说尽一部《华严经》。」大师答:「猫儿突出时又如何?」王侍郎无话可对。大师替他说:「走却法师(指老鼠),留下讲案。」并写下这样几句颂言:「老鼠唧唧,华严历历,奇哉王侍郎,却被畜生惑!猫儿突出画堂前,床头说法无消息。无消息,大方广佛华严经,世主妙严品第一。」
侍郎左宗郢问:「念佛能大彻大悟吗?」大师说:「返闻闻自性,性成无上道,又何疑返念念自性耶?」
仁和县令樊良枢问:「心乱妄想多,如何能得到清净?」大师说:「置之一处(心住一境),无事不办。」
有人问大师:「为什么不看重预知先见?」大师说:「比如二人共读《琵琶记》,其中一人没读过,而另一人先已读过,最后二人一同读完,能增减一出戏吗?」
慈圣皇太后非常崇重三宝,读了大师的《放生文》后,赞叹不已,派遣内侍,带着紫袈裟和大批银钱,前来供养,请问法要。大师拜受后,回信作答。
大师十分悲悯地狱、饿鬼之苦,大师而自习焰口,时时亲自主持设放。经常有人见到大师在法座上现出如来宝相,这是大师观想之力化现而成。
大师天性朴实、简洁、平等,言语打扮无半点虚假修饰,对事对人虚怀若谷。面相温文单纯,体形弱不胜衣,而声音犹如洪钟。胸中没有半点机巧虚伪心,而守护这颗心就像面临敌人的危城,胜过坚兵。真是善于贮藏他的经天纬地之才。大师经手银钱等事,无论钜细,滴水不漏。即使是筹划丛林中日用钱粮,量入为出,斟酌厚薄,考核因果,发明罪福,养老治病,公待众僧,不渗半点水分。自建立寺院以来五十多年中,从没有胡乱花过一文钱。
寺中僧人经常多达百人,却从不派专人乞化,听任施主自己上门。稍有一点盈余,总是布施给其他寺院,库中从不留储蓄。凡施主供斋之外,另有金银布施,接手之后,转手散去。施衣施药,救济贫病,没有一天中断过。偶尔有人翻阅账本,见最近七年之中,除基本建设及僧人用度之外,总共花费五千余两白银,每年的支出可想而知。
大师生平特别珍惜福报,曾手著三十二条警语以自勉。到垂老之年,仍然自己洗衣服、倒尿盆,不愿让别人代劳。终身布衣素服,一顶麻布帏帐,本是母亲去世那年做的,直至他自己往生时还在使用,其他东西可以类推而知。
总结大师一生的思想言行,以平等大悲,摄化一切,不是佛说的不说,不是佛的样子不学,不是佛事不做。佛嘱咐末世护持正法之人,要以四安乐行为师,大师以自己的实践完成了佛的嘱托。我们历观东土净宗历代祖师,特别提倡念佛法门,并不都是万行皆修。若是从万行中以彰一心、在尘劳中而见佛性之人,从古至人了。先代儒家称寂音和尚为僧人中的班超和司马迁,大师则可说是佛门中的周公与孔子,因为肩挑大法即是荷担大道。大师之才,足以规治天下;大师之悟,足以传佛祖之心;大师之教,足以因才观机,因机施教;大师之戒,足以护持正法;大师之操守,足以激励世人;大师之规章制度,足以救治当时佛门中的弊病。至于大慈与众生之乐,大悲拔众生之苦,广运菩萨六度,无时、无处、无事、无理,莫非菩萨之妙行。自大师发心出家以来,没有一人能对大师的一言一行提出评议,真可谓是法门中得到佛陀全部家传的人!如果不是法身大士化入人间,以自身威光照亮末法重重昏暗,又怎能这样呢?
临终前半个月,大师预先入城,告别各位故友及在家弟子,但只是说:「我要去别的地方了。」回山之后,连续几日下斋堂,亲自操作茶汤设供,并与众僧话别:「我不在这儿住了,要去别处。」七月十五日,本该设盂兰盆会,以追荐各自的祖宗父母。大师说:「今年我不参加法会了。」在寺院的记事簿里,大师悄悄写了几句话:「云栖寺住寺僧人,代堂上莲池和尚,追荐沈氏宗亲。」事过之后,人们才知道,这是大师在提前安排后事。
七月初一晚上,大师进入大堂坐下,嘱咐大众说:「我的话大家可能不爱听,我就像风中的灯烛,油尽灯干了,只等一撞一跌,才相信是真的。明天我要出远门了。」众人劝大师留住人间,大师作「三可惜十可叹」以警策大家。淞江居士徐琳等五人当时正在寺里,大师就让侍者送了五份遗嘱给他们。第二天夜里,大师在方丈室里,示现轻微疾病,闭目养神。城中诸位弟子赶到,围绕着大师。大师睁开眼说:「大家要老实念佛,不要装模作样,不要标新立异,不得坏我规矩!」大家问:「大师之后谁可主持寺院?」大师说:「戒行双全之人。」又问「目前由谁主持合适?」大师说:「以戒德高下推定吧。」说完,面西念佛,端坐而逝。此时正是明朝万历四十三年七月初四午时。
大师生于明朝嘉靖乙未年间,世寿81岁,僧腊50年。大师自己选定在寺院左边岭下,作葬身塔庙之地。大师出家前的夫人汤氏,也已在大师出家之后削发为尼,建立孝义庵,为女丛林主持,已先一年辞世,葬身塔庙就在云栖寺外的右边山下。
大师的得度弟子广孝等,是最初上首弟子。所有大师门下受戒得度弟子,不下数千,这还不算在家众。官吏士君子列入大师门墙的,也以千计,只是没有私塾弟子。
大师的著述《云栖法汇》一书,真是度世的宝船、法门的柱石。其中经典注疏及《竹窗随笔》等20多种著作,都风行于天下。大师平日教诫弟子:贵真实修行,勿显示神异。所以大师的许多神奇故事,未曾记载流传。
世尊深念末法众生难以度化,恐怕中断佛的慧命。所以在灵山会上,那些请求护持正法、亲蒙如来授记的大德,都不敢入五浊恶世度生。唯有从地涌出的大菩萨众,一力担当,对佛说:「我等末世持经,当具大忍力,大精进力,即有现身此中,亦不自言其本,泄佛密因,但临终阴有以示之耳。」观察大师一生之行事,潜藏神通,悄然运用,安住于忍辱精进之力,莫非是从地涌出大菩萨之一,或者是净土诸上善人乘愿再来的。要不然,从凡夫地起修,求自利尚且不足,又怎能广行利他,护持正法,自始至终无缺无漏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