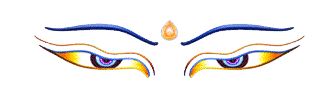罗勃特.杰克门(Robert Jackman阿姜 苏美多),一九三四年生于美国华盛顿州的西雅图。大学毕业后,入伍美国海军,韩战中担任医务官的工作。回到校园继续进修,一九六三年在加州柏克莱大学取得南亚学的硕士学位。一小段时间服务于红十字会之后,又前往远东的婆罗洲为和平工作团工作,在那儿教了两年英文。
一九六六年,对佛法日益加深的兴趣将他带到了泰国,寻求体验出家僧团生活的机会。他在侬凯省(Nong Khai)的一间寺院出家为沙弥,一年后(一九六七年),依昭坤拉迦普利迦亚穆尼(Chao hun Rajapreechayamuni)为戒师受具戒成为比丘(bhikkhu)。受戒后,他被带去见阿姜.查,留在那儿,并接受阿姜.查的训练达十年之久。期间,一九七四年,阿姜 苏美多曾至印度朝圣(以行脚乞食方式-tudong),接着(一九七五年),开始建立国际丛林寺院(Wat Pah Nanachat),并成为该寺首任住持。
一九七七年,阿姜查受英国僧伽会(English Sangha Trust)的邀请访问英国。他带着阿姜 苏美多同行,看到当地信众对佛法的兴趣,阿姜.查将阿姜 苏美多留在伦敦(汉普斯特精舍Hampstead Vihara),负责带领一小群比丘。一九七九年,比丘们移到萨斯克斯(Sussex)--开始建立戚瑟斯特佛法道场(Chithurst Buddhist Monastery)。人们对佛法的希求方兴未艾,因而,在阿姜 苏美多的指导下,位于伦敦附近的阿玛拉瓦第佛法中心(Amaravati或译为阿摩罗婆提--义译为不死(甘露)之护)也于一九八四年建立。同时,英国的北部、西南部、以及瑞士、纽西兰的分院也相继建立。
一九八一年,阿姜 苏美多被正式指定为授戒师(Upajjhaya)。他并且曾经担任伦敦的佛教协会(London-based Buddhist Society)会长(一九八三--八七)。
(译者按:阿姜 苏美多现仍为阿玛拉瓦第佛法道场(Amaravati Buddhist Monastery)的住持。)
《如其本然》
底下的开示,是阿姜 苏美多一九八八年在阿玛拉瓦第佛法中心冬安居期间,对住众所作开示的前两篇。
一个觉悟者的心是柔软而善顺一切的;
而愚痴的人啊,他的心却死执不放。
今天是一月份的月圆日,也是我们冬安居的开始。今晚我们可以彻夜禅修,坐在这儿一起祝愿此次的冬安居能够吉祥圆满。有像这样的机会,每一个人完全地投入,两个月当中专注在特定的一个法的思惟与观照上,大家能有这样的因缘是相当幸运的。
佛陀的教导就是对一切事物所呈现的实相的一种洞彻与了解--而这种事物的本然,是可以看得到的,可以了知的。也就是说发展专注、明白、欢喜和智慧--增上我们称之为「修行」的「八正道」。
现在,当我们说开始观照事物的本然,我们要在此时此刻能觉察、能看到,而不只是隔着一层「我见」的面纱来诠释它。我们每一个人所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障碍就是「我是……」--对我见的执着;这个有害的障碍通常是不着痕迹的。在我们身上,它是那么地根深蒂固;就好比鱼在水中,鱼的生活是从来离不开水的,但鱼儿却始终不曾留意到它。从我们出生开始就优游其中、未曾暂离的「感官世界」也是如此。如果我们不花些时间来观察,看清楚到底它的真实相是什么,那么一直到死,我们还是无法变得有智慧些。
不过,有机会出生为人,的确给我们带来极大的优势,因为我们能够思惟、观照我们向来优游其中的水,我们可以观察感官这个领域,如实地看看它。我们不用想去除掉它,也不要加上更多东西使它变得更复杂;我们只要保持觉知它如实呈现的本然。我们不再被这些表相、恐惧、贪欲和所有我们在心中所创造出来的东西所欺骗。
「它是什么,就是什么--它如其本然。」--就是这个意思。如果你问问游在水中的人们:「水像什么?」他们自然而然会去注意到水,说:「喔,它像这样子,它就是这样子嘛!」。你接着问:「能不能说得清楚些?它是湿的、冷的、温的、还是热的……?」这些都可以用来形容它,水可以是冷的、温的、热的、舒服的或是不舒服的……;但是事实上,它只是「像那样」本身。我们一生当中所置身其中的感官世界,它就是如此,「如其本然」罢了!你去感觉它,有时觉得它舒服,有时觉得它不舒服,大部分时间是无所谓舒服不舒服;然而,它一直就只是它本身--如其本然。事物来了去了改变了,没有任何事物是完全牢固得让你可以依靠。感官的领域也只是能量、变化和移动,都只是流动。感官的意识也都只是如其本然。
现在,我们不是要评断它,我们不说它是好的还是坏的,也不说你该喜欢它或不该喜欢它;我们就只是拉回注意力觉知着它--就像觉知水的存在一样。感官的世界就是感觉的世界,我们出生进入这个领域当中,同时我们感觉着它。从我们的脐带被剪断的那一刻开始,生理上我们就是个独立的个体,肉体上不再与任何其它人有所牵联。我们会觉得肚子饿,感觉舒服,感觉疼痛,热或冷。当我们慢慢长大,我们感觉各种事物,我们借着眼、耳、鼻、舌、身、和心本身来感觉,我们具有能够去思考、记忆、觉知和构想的能力。所有这些都是感觉(受)。感受可以是相当有趣、相当棒的,也可能是忧愁、沮丧、不舒服、痛苦的,或者它是中性的--既不舒服也不痛苦的感受。因此所有感官上的碰撞都只是「如其本然」。愉悦的,是「如其本然」,痛苦是「如其本然」,既不舒服也不痛苦的感觉也是「如其本然」。
要能够真正地做到这样的观照,你必须保持相当的专注和警觉。有些人认为只要我告诉他们事实是如何如何就行了:「阿姜 苏美多,此刻我该感觉如何呢?」然而我们不会「告诉」任何人它到底是如何如何的,我们只是打开心怀并且接受它是如何如何的事实。当他们可以为自己发现「实相」,就毋需靠你告诉任何人它如何如何。因此,去发现事物本然实相的这两个月时间,是相当相当宝贵的因缘,大家要珍惜。同生为人,有很多人甚至不知道像这样子智慧的发展是可以做到的。
当我们使用「智能」这个字时,到底是指什么呢?从出生到死亡,这就是「如其本然的实相」。人生总有一些痛苦、不舒服、不如意和丑陋--如果我们不能如其本然地去认识、觉知它--不能遵循法的教导来看待它--那么我们必然由此创造出一些麻烦。出生到死亡之间,变得非常自我,伴随着种种的恐惧、贪欲和困难。
在人类社会里,「寂寞」让我们受苦不少。我们生活中有多少的尝试就为了能让自己不寂寞:「让我们彼此交谈,让我们一块儿做事,我们才不觉得寂寞。」然而不可避免的,我们与生俱来带着这身人类的躯壳,就注定是孤单的。我们可以假装,我们可以娱乐彼此,但那也是我们所能够做的了。当生活中有了真实的体验,我们就会知道:自己本来就是非常孤单的;而我们却过分期待别人可以将我们的孤单寂寞给带走。
你看,当我们的色身一出生,自己似乎就是和其它分开的一个独立个体。你我每一个人肉体上都没有相连在一块儿,不是吗?由于对这个身体的执着,使我们觉得孤立和脆弱;我们害怕孤单寂寞,于是划筑出一个属于自己能够安住的个人世界。我们有形形色色各种新奇有趣的朋友:想象中的朋友,物质上的朋友,敌人……等等,但是所有的朋友却都是一样地来去、开始和结束。每一件事物,都在我们自己心中生起而后逝去。因此我们要这样思惟:生缘死--出生带来死亡;生起和逝去,开始而结束。
在这次冬安居期间,我非常鼓励你们如是观照:专注观察到底「出生的是什么」?现在我们可以说:「就是出生后的产物--这个身体啰!也包括了它的意识和感觉,还有智力、记忆和情感。」所有这些心的内容和作用,也都可以用来观察,因为它们也都是「法」。于是我们知道,如果我们执着这个色身,为这个色身所奴役;或者执着意见、看法和感受,当成是「我」、「我的」的话--我们就会感到寂寞和绝望,而导致对分离和结束怀有恐惧。对于不可避免的死亡有了执着,就会将恐惧和贪欲带入我们的生命。即使我们的生活一切如意,我们还是会感觉到那一丝的忧虑和担心。只要有无明(愚痴无知)--avijja--根据事物的真实法则,恐惧担忧终究支配着我们的意识。
然而,「忧虑」到底不是真实的,它不过是我们创造出来的。担心也只是「这么多」罢了。爱、喜悦和所有生命中最好的,如果我们有所执着,也会带来负面的结果。这就是为什么在禅修中,我们要练习去「接受」这些感受。当我们接受了事物所呈现的本然,我们就不再执着它们。它们只是如其本然的它们,它们生起然后灭去,它们不是一个不变的本体。
现在,回到我们所处的文化背景,来看看原本它带给我们的观念是如何的?我们的社会倾向不断地增强每一件事物是「我」和「我的」的这种观念--「这个身体是我,我看起来像如何如何,我是男的,我是美国人,我五十四岁,我是一间寺院的住持……」其实,这些都只是约定俗成的习惯和世俗需要而说的,不是吗?我们并不是说这些都不是事实、都不是我,而只是想点出我们要观察一下自己是如何地因为相信「我是……」而惯性地让这些事实变得复杂。如果我们对这些产生执着,我们的生命就远比「实际只是如何」多出太多太多,它变得彷佛一张具有黏着性的网一般,变得非常复杂,碰到什么就黏着什么;活得愈久,我们就制造出更多的困惑。这么多的恐惧和贪欲就是从「我是……」而来--从「是某某人」而来。最后的结果,带给我们忧虑和绝望,生命似乎远比「它实际只是如何」要来得困难和痛苦太多。
而当我们就只是如其本然地观察生命,那么你会发现其实一切都好好的:欣喜、美丽、愉悦,就是这样;痛苦、不适、生病,也只是实际的那样。我们始终能够平常心地面对这种生命迁动和变化的轨则。一个觉悟者的心是柔软、顺应而随处自在的;而愚痴的人们,他们的心却任由环境摆布,坚执不舍,注定烦恼。
我们所死执不放的终将导致痛苦与不幸。男人也好,女人也好,如果你坚信它的永恒不变,常常只会给生命带来困局。我们所认定的任何阶级--中产阶级、生产阶级、美国人、英国人、佛教徒、上座部佛教徒……等等--紧握这些标签和意像不放,将产生某种的困惑、困难、沮丧和绝望。
然而,依世俗的需要和习惯来说,一个人可以是这些名称--一位男士、一个美国人、一个佛教徒、一个上座部的佛教徒。这些都只是心的分别作用下的产物。这些都是因为沟通上的需要;这些名称存在的意义就仅只于此。它们就是一般所说的sammuttidhamma--「世俗的实相」。当我说:「我是阿姜苏美多」这并非有个自我的个体,并不是一个人,它只是一个世俗的名称。作为一个佛教的僧侣也不是一个人--它是一个世俗的习惯称谓;是位男众也不是一个人,只是世俗的说法。世俗的名称也只是世俗的名称,原本也无妨无碍;但是当我们出于愚痴地执着它们,我们就变得划地自限而自缠自缚。这是一张黏着的网,我们睁着眼瞎了,被这些世俗的名称所欺骗。
当我们能够放下这些世俗的约制,不代表我们要将之丢弃。我们不用丢掉它们,我没有必要自杀或者还俗,这些世俗的名称一点也不打紧。只要我们的心是醒觉的,看清楚它们到底是什么的话,这些世俗名称就不会挟带着痛苦与烦恼;它们就只是它们--如其本然。它们只是一个方便,因时因地的权宜方便。
如果对「究竟(胜义)的实相」(paramatthadhamma)有了体验,便有涅盘的解脱。从贪欲和恐惧的迷惑当中解脱出来,这种超越世俗约制的解脱便是不朽的永恒。但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得真正彻底地看清楚执着的真面目才行。哪些执着呢?痛苦是什么?对「我是……」整个过程的执着又是什么?这个执着到底是什么!?我们并不是要人们去否定他们自己,否则,执着自己「什么人也不是」的观点,就仍然避免不了是「某种人」。这不是加以肯定或予以否定的问题,而是真正明了、实现、和亲见与否的问题。要达到这个目标,我们要发展「念住」。
借着念住的功夫,我们能够对于无法避免的死亡敞开心怀接受它。冬安居一开始,我们就要展开双臂迎接这整整两个月。第一天,我们已经带着完全的觉知准备接受一切的可能:生病或健康,成功或失败,快乐或痛苦,觉悟或是完全地绝望。我们不会去起这种念头:「我只要得到……;我只想有……;我只希望美好的事情发生;我得好好地防护自己,享受这次安祥美好的静居生活,两个月内完全地宁静而不受干扰。」这些念头本身就是一种痛苦的状态,不是吗?取而代之的,我们接受所有的可能,从最好到最坏的情况都能接受。我们要清楚明白地这样去做,也就是说:两个月当中所发生的每一件事都是我们这次安居静修的一部份--它是我们修行用功的一部分。「如其本然地接受每一件事物」,对我们而言这就是「法」:不论是快乐或痛苦,觉悟或完全的绝望--每一件事物!
如果我们这样地练习,那么绝望和极度的苦恼将带领我们达到宁静与安祥。从前我还在泰国时,曾经有过许许多多负面的心态--寂寞、无聊、焦虑、疑问、忧愁和绝望。而当我如其本然地接受它们时,它们就停止。不再有绝望时,还会剩下什么?
此刻我们所谈论的「法」,的确是细微而难以了解的。但也不是说,它是那么地遥不可及、高不可攀--其实它就这么平常,就在此地此时,而我们从来没注意到它。就像水之于鱼的意义一样,水在鱼的生命中绝对是最重要的一部份,而牠却从来不曾注意,即使牠一天到晚优游其中。同样的,感官的意识就在这儿、就在此刻,它本来如此。它一点也不远,真的毫不困难,你只消专心地注意着它就是了。脱离痛苦的方法就是「念住」:念住的「觉知」或「智慧」。
因此,我们就不断地注意着事物的本然。如果你有了不好的念头,或者感觉怨恨、苦涩、恼怒,那么就看看它在你的心中感觉起来像什么。如果你此时觉得沮丧和忿怒,没关系,因为我们早已准备好允许它们的到来。这是修行的一部分,接受一切事物如其本然的实相。记得,我们不是努力地要成为天使或圣人,我们不是试图去摆脱所有我们的不净和染着,我们也不是只想保有快乐。人类的世界本来「如此」,它可以是非常粗鄙,也可以尽是清净。清净和不净一体两面,明了清净和不清净的,是具足念住的智慧;明了「不净」是无常的和无我的--也是智慧。但是呢,我们将它视为「我的」那时候--「喔,我不应该有不净的念头!」--我们就再一次陷入绝望的沼泽中。我们愈是只准自己存在清净的念头,更多不净的念头就会不断涌入;保险这整整的两个月我们将变得痛苦不堪,我敢保证。离不开愚痴无明,我们为自己所创造出来的世界注定是痛苦与不幸。
因此,在所谓的念住(觉知)、或者完全的念住当中,所有的痛苦和一切的快乐--它们的价值是平等的,没有说哪一个你比较喜欢。快乐是如此,痛苦也是如此;它们都同样生起然后停止。快乐仍然是快乐,它不是痛苦;而痛苦也依旧是痛苦,它也不是快乐。不过呢,它是「如其本然」--它是什么,就是什么。它不属于任何人的,它就仅仅只是那样--只是如其本然。而我们不会为它所苦,我们接受它,我们知道、我们了解它。一切生起、消失,诸法无我。
谨以此供养大众,善思之!
阿连·亚当斯(Alan Adams契玛达摩法师)一九四四年生于英国的朴次茅斯(Portsmouth);为了成为一位演员而受训于戏剧学校。七年的演员生涯中,他走过世界上很多地方(包括一次在美国长达一万四千里的巡回演出),而有三年时间待在国家剧团。后来对佛法心生兴趣,最后决定前往泰国出家成为比丘。
一九七一年在摩诃塔特寺(Wat Mahathat)随昭坤殿普·悉度玛尼(Tan Chao Khun Demp Siddhumani)剃度为沙弥。一年后他到巴蓬寺(Wat Pah Pong)去,受了比丘具足戒(一九七二年)。一九七七年,他陪同阿姜 查和阿姜 苏美多去英国,而后就在汉普斯特精舍(Hampstead Vihara)住了下来。其间,他对教化监狱里的囚犯一事产生兴趣,阿姜 查也鼓励他。几年下来,这个工作持续成长,而于一九八四年,契玛达摩法师设立了一个佛教监狱弘法(布教)工作机构“鸯掘摩罗”(Angulimala)。这个机构得到内政部的正式认可,荣誉导师包括沙达提沙法师(Ven. Dr.Saddharissa)、僧伽拉克西塔法师(Ven. Sangharakshita)、阿姜 苏美多(Ajahn Sumedho)和艾瓦伯瑞勋爵(Lord Avebury)。
契玛达摩法师他在怀特岛上自己建立的精舍待了五年,其间,英国广播公司(BBC)制作的纪录影片<In.More Ways Than One>当中曾经介绍过他。一九八五年,他移到瓦立克郡(Warwick Shirc )现在的住所森林静居(the Horest Hermitage)。一九八八年在那儿盖了一座佛塔,有“英国大金塔”之称(English Shwe Dagon)。目前(一九八九)他和几位比丘共住,继续监狱弘法,指导禅修,并且定期在瓦立克大学空中大学节目上讲授佛法课程。
译者按:契互达摩法师现仍为英国森林静居(the Horest Hermitage)的住持。
面对痛苦
这篇开示,是契玛达摩法师应「Caduceus」杂志之邀所写,於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刊出。
(译按:Caduceus是古希腊代表医生的一种标志,在此为一医学杂志名。)
内观(洞见)修行利用每一个事物,
它将每个事物化为成就的契机。
〔节译〕
佛陀提到十二种苦,也可以缩为三种苦,或是根本的一种苦。十二种苦是:生、老、死、哀、悲、苦、忧、绝望、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五阴(蕴)炽盛。三种苦是:一般疼痛和痛苦的苦(苦苦),无常的苦(或谓变坏逼恼之坏苦),执取五蕴的苦(或谓众缘所造、生灭迁流之行苦)。一种苦是:依缘(条件制约)的存在是苦——或者说五蕴就是苦。
大部分说来已很清楚了,但也许我最好再将这似乎神秘难解的五蕴解释一下。这是佛法当中对一个人的分析。五蕴是:色蕴(形体),受蕴(感受),想蕴(分别),行蕴(习性的造作),和识蕴——没有一个是坚固稳定、恒久、或是由任何不变的自体组成的。我们有时会将它们说成一个心理和生理之间的互动过程。形体,显而易见的是指身体:它只是一些物质,无数不断振动的粒子团,不断地在形成和破灭的过程中;它没有知道任何东西的能力。剩下的四个:受、想、行、识——相当於心的部分,能够知道事物。五蕴是依赖其它事物而有的,而彼此也依缘而存在。五蕴在一起而创造了—个个体——一个组合的个体,就好比天空中翱翔的飞机或天鹅—般,处於内部构造不断地相互影响、作用,和对外在条件不断回应的—种状态中。
因此,心影响著身,身影响著心。这个组合的个体依靠条件而生起,它根据条件而生长或发展,也因条件持续而持续。心的部分包括了认知(看、听、嗅……等)的作用(识蕴)、分别的作用(想蕴)、愉悦或不愉悦感受的作用(受蕴)、和贪嗔喜恶的作用(行蕴);而这些心的作用得仰赖根门(眼、耳、鼻……)、对象(尘境)、和两者(根尘)的「接触」——这三个条件具足,才会接著发生。以眼根为例:没有眼睛你看不到;没东西(对象)你也看不到;面向前方,眼睛就看(接触)不到背後。如果,你发展了觉知力,在禅修当中培养了内观的洞察力,你将会看到你的世界,你的经验的整个范围,其实就只是这「五蕴」;而「苦」则来自於你对它们的执著——来自於这个不健康的心态。
我们的经验世界是这些「蕴」复杂的运作:心依色身而住,经由根门和对象(尘境)接触时而生起,伴随著对尘境的认知、分别、生起感受、接著习惯性的反应,来为这个经验赋予了色彩。这些过程发生之快,就好比将一些静止的画面(照片)或声音的振动快速传动所产生的结果一样,不过是一种错觉罢了。这是自我的一种错觉。
为了明白这个事实,你必须慢下来,仔细地观察你自己。继续观察下去,你将会看出现象本身,只是不间断的一种流动,没有实质的物质存在,都只是不停地移动;而如果你试著去执著、抓取或排拒它,必然带来挫折和沮丧。观察这些念头、感受和经验的整个过程,「自我」便会开始褪去,对自我的「执著」也同时减低。心态的转换和一种跳脱的自在逐渐产生;你开始明白事物的真实特性(实相)。内观洞察力的累积便是智慧的建立。了知事物如其本然的实相,满足之心生起;你既不会想去改变它也不会贪执它——这便是一个健康的心态。
佛陀初转法-轮时所说的四圣谛,事实上是他在达到完全的觉悟之前,必须彻底了解、用功、体验和明白的。四圣谛是:苦;贪爱——苦的起因;苦的止息;和达到苦的止息的道路(方法)。佛教的治疗方法最重要的就是对苦的回应;和包括道德生活、心的训练和智慧的—个完整方法。
对我们而言,在心的训练当中,「禅修」是最重要的练习——这是让心宁静和澄清净化的过程。你可以想像沉没在湖底的珍贵珠宝:当狂风暴雨激起了骇浪惊涛,你完全无法往船边的湖面仔细搜寻,没有机会赞美闪亮耀眼的宝石。泥沙让湖水混浊,汹涌的波浪拍打著船身激起水花,再耀眼的宝石依然完全晦暗。但是,一旦暴风雨过去,湖面转为宁静澄澈,泥沙沉淀;毫无困难,你可以安稳地划过湖面,往两边仔细察看。现在,绚烂夺目地足以令人眼花撩乱——宝石毫无阻隔地绽放出光芒。
同样的,混乱和波涛汹涌的心让我们原有的智慧失去光明而晦暗。当然,要在心上用功,要处理心的问题,可没像湖中珠宝这个比喻那么简单。毕竟,智慧的缺乏,助长了奔忙不息的心;使得我们没有办法静静地坐在那儿,等到心自自然然地安静下来。还好,禅修可以帮助我们——禅修的训练包含了专注和洞见(内观),或者说是宁静和清楚——二者同时作用,也彼此增上。在「森林静居」这儿,通常我给的建议是:先以慈悲观的专注来让心宁静下来;接著才是毗婆奢那(Vipassana)的练习,也就是所谓的内观禅修——这是经由念住的培养才得以发展的。
当我们坐著禅修,会经验到痛苦的感受。它也许像针刺,或是膝盖的疼痛;也可能是不愉悦的心念或记忆。用功的方法和处理的方式,端看在你的修习中强调的是什么:要看是强调专注还是内观。这两种情况当然都可以看到痛苦,但是如果只是单纯地训练专注、让你的心宁静下来,那么你的工作就是要避免停在苦受上,藉著回到你禅修的所缘上来加大、加多专注的强度。
练习慈悲观,以慈爱的心来看待痛苦会有所帮助;这会软化你对於痛苦的态度,并且把你带回到禅修的所缘。在专注的修习当中,痛苦对你而言形同一种阻力;你会明了这样地处理阻力(忽略它,而拉回到专注的所缘),对於你正在做的,将带来能量和让你的心更加锐利。请您务必清楚这并非一种压抑,你不要想去否认你的痛苦或者甚至想排除它,你只要以更大的强度专注在你的禅修所缘上;以这种已经形成的痛苦——藉著这种阻力来鞭策自己。
而当你发展内观(洞见)时,则把痛苦当作念住的对象、看著它。内观的练习最重要的是发展一种专注的「觉知」;对於每一个经验都只是保持「知道」。这样的过程,有各种不同的方法(技巧)可以帮助你;而你最好能熟悉这样的修习,如果你了解了、有了兴趣,就在正确和适当的引导下练习下去。只要以这种方式看到了痛苦,它便失去了力量。有时候它会完全都不见了,如果没有,你只要觉知它只是感觉,只是感受,你放松,那么不舒服就会减轻。然後,你开始检视它,你会发现它不是「痛苦」,它不是个静止不变的「东西」,而其实是各种经验不断在改变、移动的一种连续过程,不断地流进流出。现在你是在洞见实相的路上。当你以这种方式用功,你更能平稳地面对痛苦,你从它身上学习。你的「痛苦」可以教你很多很多;你将看见它不曾刹那静止;你会明白:由於你的恐惧和不喜欢而促成了它,你甚至还抓著它不放,而且隐藏其後的那个愚痴无明的心总是希望它们(痛苦)不要那样——这种不健康的心态。突然间,这些可怕的经验正转为你的成就因缘,你一步一步地赢了。
这就是内观(洞见)修行的美好;它利用每一个事物,为每个事物带来作用和生命,将每个事物化为成就的契机。无论什么感受、什么经验生起,你的责任就只是提起注意力观察著它。不用对它作任何事,不要在心中加上任何欲望——希望它变一变;而是要对於事物所呈现的,觉得满足,念住地看著它就好。日常生活当中也一样,要念住、保持觉知、看著它而满足。事物就是如它们所呈现的,它们不可能是其它。之前它们也许可以是,但是它们现在就不是。它们是如其本然。未来它也许会完全不同,但是此刻它就是如此,它如其本然,它很好。它就是我们此刻确实有的全部,没有别的了——在这儿,我们将发现智慧的踪迹。因此,放下有所得的心,只留下满意、知足,保持念住,明了事物的真实特性(实相),具足一个健康的心态。放下吧!愿您快乐。
列德·培理(Reed Perry巴山诺法师)出生于加拿大曼尼托巴的拉巴斯(La Pas,Manitoba)。他在温尼伯大学(the University of Winnipeg)念历史系。毕业后,在印度旅行了一段时间;然后从那儿去了泰国。
一九七四年,为了得以继续待在泰国,他决定利用出家身份来达到这个延签的目的。于是他在普连毗婆奢那寺(Wat Pleng Vipassana)依若纳西立瓦塔那法师(Phra Khru Nanasirivatana)为戒师受了具足戒而成为比丘。没想到,他却开始对寺院的修道生活产生兴趣。出家的第一年,他的老师就带他去见阿姜 查;他因此请求允许留下来并接受训练。
巴山诺法师是国际丛林寺院(Wat Pah Nanachat)最早的住众之一;出家后的第七年担任该寺的住持。在他任内,国际丛林寺院无论在规模上或是在声望上,都有相当大的进展。在泰国,巴山诺法师已成为众所皆知、受人崇敬的一位法师。
译者按:巴山诺法师现为美国无畏山佛法道场(Abhayagiri Buddhist Monastery)的住持。
什么是重要的
这篇开示译自泰语,是巴山诺法师於一九八七年九月,在曼谷附近的佛陀蒙通 Buddhamonton(Buddhamandala佛坛)以泰语所作的开示。当时正值泰皇菩弥博陛下(His Majesty King Bhumibol)六十大寿庆典前夕,而在一场作为献礼的——为期一周正式的禅修指导与修道会当中,所作的开示。
如果在我们心中,少了实相真理的富有,
那么当我们死了,他们一把火将我们火化了,
我们生命的价值
不过是我们制造的那么一点骨灰罢了。
佛陀贡献他的教导给这个世间,目的是为了呈现一条明了实相(谛、真理)的道路——法。他一生的舍离,我们才得以亲身明了这个实相。就事实而言,这些教导仍然在我们身边;这也显示:这些教导长久以来一直为人们(包括出家在家)所善用著。然而有件事很重要,我们必须了解:亲身去思惟、体验这些教导,而让它们的真正价值得以显现——这是必须的。以这样的亲身思惟和体验,如果做得正确,我们会明白这些教导所贡献的圆满、清凉和宁静。
身为外国人,待在泰国这儿,我发现过著这种佛教僧侣的生活相当地有益处。有时候人们到我们的寺院国际丛林寺院来参访,问我出家多久了,我告诉他们:「超过十年了。」他们总会问:「出家生活好吗?」我回答:「如果没有一点好,为什么我要花超过十年时间过这种日子?我有很多其它事可以做的,不是吗?」这是因为我「亲身」看到了自己所生活的这个方式(这条正道)——它的价值所在。
如果对自己内心的过程没有清楚了解,我们就会创造出各种问题与麻烦。我们变得激动、烦恼、被各种情绪拖著跑。为了达到个人和全球的和平,我们必须明了这些状况:必须看清楚内心的运作习性。这便是法的作用与价值。
思惟佛法的正道时,有件事很重要:我们必须明了绝对没有所谓的义务或胁迫这回事。这条正道,我们可以选择走或不走;关於这一点,我们有完全的自由——佛陀只是提供我们、将这条道路介绍给我们。没有个外在的审判官在检视我们,看我们走或不走。他只是指出什么会导向真正的成功、导向解脱、安祥和智慧;也指出什么会导致失败和困惑。没有任何外在的权威正在作绝对的声明: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对或错;如果我们选择不跟随,也没有人会惩罚我们。不过呢,要观察——观察在我们的心中,那个总是在那儿的、总是知道我们正在做什么的那个东西。
因此,重要的是,我们得一起思惟看看,如何真正地利用佛陀的教导而让自己能够明白佛陀教导的真正价值。关於四圣谛和八正道,我们都已经听过很多次了。也许我们听著听著,只是将之视为当然、有这么回事罢了;我们认为它们不再那么重要了。但是,这些教导事实上却是关於「佛陀正道的核心」。佛陀四十五年的教化,他未曾改变或丢弃它们。
上个星期在我们寺里,我因为扭伤脚踝而没办法跟大众一起经行禅修。静坐时段我和大家一起共修,接著的经行时段,我就回到自己寮房。我利用这些时间温习一些我们平日唱诵的经文。有很多次我读诵了佛陀的第一次说法——初转法-轮经(the Dhammacakkappavattana Sutta)——经中包括了四圣谛和八正道。结果我发现了许多很有价值的重点。
让我们首先想一下佛陀给予这些教导时当时的时空背景。佛陀花了六年的时间苦修奋斗,终於亲证了实相(谛、真理)。他经历了难以想像的各种困境——不像近来的一些修行人,只要有一丁点的条件无法确实地如其所愿,他们就显得大惊小怪、起无谓的烦恼。当佛陀最後达到圆满的觉悟时,他慎重地思惟要如何确实地分享自己的证悟与了知。当时他三十五岁,正值盛年,年纪并非老迈——而且,当年在王宫里受过最好的教育,他完全足以言语清晰地表达所了悟的。因此,他还用不著急切地逢人便教。
他决定了:当时自己坚持苦行时跟随他的五位同伴是最适合的人选。他们完全真诚地投入精进修行,很有经验,也具足智慧。於是他走了好几个星期到达他们停留的地方。来到他们跟前,佛陀给了四圣谛与八正道的教导。由此可见,这些教导(这次的说法)并非平常,而且是具有相当重大意义的。
事实上,关於这些教导我们已然听过、谈论过很多次,意思是说,我们正冒著险——让这些教导对我们而言变成仅仅是理论而已。然而,就算以世间来说,当我们谈到成就某件事物,我们也会了解,要成就当然需要精进;更不要说是八正道。只要我们有正精进,对正道的了知就能实现。
现在,让我们思惟一下所谓的「正精进」是指什么。佛陀说了一个把一根小树枝丢到河里去的譬喻。如果那根小树枝不靠左岸或右岸搁浅,也下沉到河里的话,那么它必然会流抵大海。以我们的修行来说,所谓的左边和右边的河岸是指两个极端:对愉悦乐受的执取——kamasukhallikanuyogo和对痛苦的执取——attakilamathanuyogo。没有沉没是指不放弃精进。如果不耽溺於愉悦的乐受、不习於对苦受产生负面情绪的反应、不放弃精进修行,我们一定可以抵达涅盘——平静。这是一种自然的法则。一种如实的认知和真诚地遵循这条道路,必定为我们带来像这样的结果。
八正道称为中道,是指我们的精进必须在松紧之间调整得当。如果我们身体和言语的行为不能在这条正道上保持和谐适中;再加上如果我们还是耽於寻求感官的乐受和习於产生生气、易怒的情绪——那么当然就不可能如实地见到事物的真相。
我们要不间断地努力保持正确的精进,否则我们到最後会像那小树枝一样沉入河底。当我们感觉自己修行的热情燃起时,我们可以很容易地保持著修行;但是有时候也可能:我们感觉完全的幻想破灭,甚至到某种程度,我们完全忘记了最初的信心与信仰的心。然而这是正常的。就像长距离的游泳一般,我们感觉累了。我们不需要因此惊慌,自然地就让它停一段时间就好了。之後当我们重获一些力量,再继续下去。不要沉没最重要!只要明了:和自然的法则一致,那种状况将会改变。绝望的心情,如果已经生起了,就—定会过去。只要保持修行。观察我们的心,看到我们自己的想法、态度是如何地不断改变,而明白了「无常」是自然的。
要了解:这种法的思惟在我们生活中是多么地需要。它就像是心的营养品,滋养著我们的心。如果没有这种清楚的了解,我们会像错失了什么东西一样。时常,人们来见阿姜 查时总会说他们没有时间修行;他们会说自己有太多的责任、太多事要做。阿姜查会问他们:「你有足够的时间呼吸吗?」他们通常回答:「噢,当然!呼吸是件自然的事。」
在法上培育、增上,和呼吸不是一样重要吗?如果我们停止呼吸就会死去。如果我们对事物如实呈现的实相没有建立起正确的了解(正知见)的话,我们也从那些真正好的、真正自在、和具足真正意义的生命当中死去。如果在我们心中,少了这种实相真理的富有,那么当我们死了,他们一把火将我们火化了,我们生命的价值不过是我们制造的那么一点骨灰罢了——就那么一点点!我们必须探究一下如何过著一种真正地合於佛陀所教导的方式来生活。那么,我们必然活在安祥与和谐当中,而没有任何冲突、困难、和解决不完的问题与麻烦。
戒(道德的生活)所显示的,正是中道的实践。它指出:避免极端的贪著愉悦乐受和对痛苦的嗔习反应——也就是说要知道正确的生活方式。当我们生活中身、口的行为合乎中道,那么我们就不会对别人形成伤害;我们只做对人类有益的。而正式的禅修练习(修行)则是要训练我们的心念、我们的心,能够安住在中道上。
很多人禅修的时候,他们试著强迫自己的心达到他们想要的状况。他们坐在那儿和自己的念头争论不休;如果他们的注意力跑掉了,他们就用力地、强行将它拉回到呼吸上。过多的强迫并非中道。中道是当我们有了正精进、正确的意向和正确的觉知时,在心中所自然生起的那种自在。只要修行是「正确的」,心安然而不过份费力,我们就能单纯地看著心中不同的状况生起并且明了它们的特性。我们不用和任何东西争吵,争论只会形成不安。什么样的情绪生起,都在我们觉知的范畴之内,我们只要单纯地看著。无论它是充满快乐的还是完全相反,所有的经验都在我们的「觉知」——它的范围之内。我们只管坐著、看著、静默专注著,不论什么生起——知道它们的生起;它们就会自然地消失。为什么它们会消失?因为那是它们的特性。就是这种对於「改变(无常)」的真实特性的了知,这种了知,强化了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更加平静。以这样的洞察(智慧panna),便有了平静(定samadhi)和安祥。
佛陀的智慧就是知道事物的真实相。不是去知道什么是什么,而是知道无常、知道苦、知道无我。我们之所以看不到事物的真实相而认为其它,就是由於我们缺乏智慧。具足了智慧,我们知道如何放下:放下贪爱、放下执取、放下很多的相信。放下我们总是将事物看成一个实体的习性。
我们称呼的「我」只是世俗的需要和习惯上的称谓;我们出生时没有带来名字。之後某人给我们取了个名字,叫了一段时间,我们开始认为那就是一个东西叫作「我和我的」真的存在。然後我们感觉我们必须终其一生照顾好它。佛陀的智慧则知道如何放下这个「自我」和一切与它有关的:所(拥)有物、态度、观点和意见。也就是说放下了苦(dukkha)会再生起的机会,或说是给予见到事物真实特性的机会。
因此,培养「八正道」,发展一切对人类而言是「正确的」的特质。透过道德规范、平静和智慧的修习(sila,samadhi,panna戒定慧),我们能够安住在和谐当中。不断地陷於极端的境况中,是因为自私的结果;是不知正确的方式、不知中道的结果。八正道是我们需要去做的一个工作。如果谨慎地且正确地实践,正确的结果必将显现。
上个星期念诵了佛陀的初次说法,提醒我八正道是如何真正地带来利益。经中这样说:「Cakkhukarani,nanakarani,upasamaya,abhinnaya,sambodhaya,nibbanaya samvattati.」意思是:藉著打开「法眼」来展开正道——cakkhukarani;产生了洞见——nanakarani;产生了平静——upasamaya;「准确地知道(明白)」生起了——abhinnaya;完全地知道(明白)——sambodhaya;了知了圆满的涅盘解脱——nibbanaya samvattati。这就是佛陀所教导的完整的一条正道。它是一条正道——当我们不断地去培养、增上,打开了法眼,我们就能见到「法」、明白「法」和成为「法」。法眼亲见了:任何因缘生起的条件也终将灭去。
经典中我们读到的,当「法眼」开了,当我们清楚地见到了诸法的实相,那么就「进入了法流」。这样的知见与亲证,唯有八正道的修习才能达到;实践八正道,让烦恼减少了,带来了心的平静安祥,而最後从所有的痛苦当中解脱出来。因此对我们而言,它是至高无上的,是最重要的。八正道的作用、利益如此——它真实不虚。
我们会如何地实践、如何地修习「佛陀的教导」,就看我们对於「佛陀的教导」的了解为何,看我们认为它的价值何在。请您试著去探究,务必让您的生活合於佛陀的正道。
阿难陀法师一九四六年生于美国纽约州的水牛城(Buffalo),而在靠近尼加拉瓜大瀑布附近长大。高中毕业后,亿就加入了美国海军陆战队,在越南担任通迅兵。在战役中严重负伤,亿被送回美国,幸运地,他最后不可思议地康复了。受勳并因伤离职之后,他进入水牛城大学念心理学和法文,也在一所天主教学院待过一个学期。
这段期间,使他从美国介入越南一事中觉醒过来,参与了一些日益茁壮的反战示威运动;最后他决定再度离开美国。在法国尼斯(Nice)一年的求学期间,他无意中看到的一本由阿连·瓦兹(Alan Watts)写的关于禅(Zcn)的书,引燃了他前往东方的兴趣。陆路之旅,途经土耳其和阿富汗,半年时间待在尼泊尔和印度,在那儿他首次遭遇到禅修。
一九七二年,由于美国军方的要求,他必须接受一次健康状况的复检,使他偶然地来到了泰国。当他停留在帕塔雅(Pattaya)的一处寺院时,有人带他到冲布里(Chonburi)的科恰罗克寺(Wat Kow Chalok)去见阿姜 苏美多。他就因此在那儿剃度成为沙弥,稍后到巴蓬寺(Wat Pah Pong)去,受比丘具足戒。
在泰国住了五年之后,法师于一九七七年回到美国探望家人。之后,改变了原本回东方的计划,在阿姜 查的要求下,加入了阿姜 苏美多在伦敦的汉普斯特精舍(Hampstead Vihara)。从那时开始,他也协助了在戚瑟斯特(Chithurst)和汉哈姆(Harnham)两处道场的建立。目前(一九八九),他是戚瑟斯特佛法道场的现任住持。
译者按:阿难陀法师后来还俗,且已过世多年。但这是一篇不错的文章,译者予以保留。
慈悲与内观
底下,是阿难陀法师的一篇开示,尤其是慈悲观的部分。
「……气息进来,充满慈悲的能量;气息出去,
祝福他人一切安好。」
经典当中有个故事。当时大约是在佛陀成就了正觉的二十年之後,出家僧团已有相当大规模的成长。当时住在拘舍弥(Kosambi侨赏弥)的一些比丘有斗诤事起。诤事激烈到原本和合的僧团几近分裂。佛陀觉得事情严重,一听到这个状况,便往那些比丘住处而去,希望能止息诤事、重建平静祥和。但是,佛陀的开示诃止竟不为诸比丘所接受,他们告诉佛陀:「愿世尊安稳而住,此时此地不劳世尊,我们自己知道如何处理。」这无异於婉转地告诉世尊:「您老人家走吧!」
几次企图重建僧团的和合无诤,都不为接受之後,佛陀离开了。
佛陀来到了般那蔓阇寺林,那儿有三位比丘弟子共住修行:尊者阿那律陀(Ven. Anuruddha)、尊者难提(Ven.Nandiya)、尊者金毗罗(Ven.Kimbila)。这三位弟子都已完全觉悟(阿罗汉——arahant)。
当佛陀抵达林中,比丘们以传统的礼节欢迎世尊的到来〔出迎摄佛衣钵、为佛敷坐、为佛取水〕(译按l)佛陀问他们:共住是否和合安稳,乞食是否不虞匮乏?尊者阿那律陀回答:「世尊,我们都没有问题,我们真的无所缺乏、共住和合。」佛陀叉问:「这怎么说呢?」阿那律陀於是向佛陀报告,他是如何地内心存念:能和这么好的修行善友共住真是莫大的功德与福报;以及他已决心舍弃个人的爱好与习惯,他将随顺於任何有助於共住利益与和谐的事。佛陀赞许阿那律陀并且进一步问他:「你们的修行生活是否勤奋精进?」阿那律陀答:「是的,世尊!我们勤奋精进。」佛陀又问:「阿那律陀,你们做什么呢?」
阿那律陀概略地描述生活中他们如何地彼此照应。例如:谁先托钵回来的,便敷座席、安置好饮水的水瓶和洗手足的罐子。用餐後,最後吃完的便收拾清洗。他们自动自发帮助彼此,填满水瓶坛罐,也取水作厕所洗净之用。〔一人可以独力做的便独自做,不能的则以手招一比丘同做,但各不相语,各不相问。〕(译按2)
每个星期集会一次,整晚共坐,或彼此论法,或默然禅修。而最具意义的一点是,在这部经中强调多次的,阿那律陀说:「我对共住的同参,常安住在慈悲的心上,〔安住在慈悲的身口意上〕(译按3),碰面时或独处时等无有异。我的心和谐地随彼同参善友的心;某个层次来说,只有同一个心。」佛陀接著询问另外两位尊者,他们回答得没有两样。佛陀於是再次地赞许并鼓励他们继续下去。(译按4)
这样的故事真的令人为之鼓舞——看到这些觉悟的圣者们,他们明白这种慈悲观(爱人的仁慈心)的修习必然带来和谐与安祥,这多么美好啊!由於他们对周遭同住者的需要,慈心的关注,为这个世间所带来的安祥和谐是明显可见的。即使从一位阿罗汉圣者的观点来看,以世间需要(世俗的)和明显的表达方式来帮助彼此,还是非常重要的。这些正是导向和谐、和合的因素。很多年来,我已然发现作这种思惟对自己相当有帮助。
在其它经典中,也提到修习慈悲(慈心)观(metta bhavana)的「十一种利益」。第一个利益是入眠容易且睡眠安稳满足。第二个利益是睡眠醒来容易、满足而愉悦。第三是为人所爱敬。第四是甚至为其他有情所爱。接下来是不为火烧、毒药、和刀箭所害。再者说到修习慈悲观令心易於专注。第九是其人安祥宁静、精神悦豫、容光焕发。第十个利益是死时心不迷惑、不颠倒。第十一个利益说,一个人即使未能往内观察去洞见心的实相,那么修习慈悲观的力量将带他出生天界。(译按5)
慈悲观的修习对我而言有个非常重要的改变,就是对自己的容忍力增长了。从这个课程中所问的问题看来,人们仍然被相同的老症状所困,依旧和「不想要如何如何」奋力搏斗。我们建立了我们所想要的,来对抗我们所不想要的。念头和幻想於是变成了敌人——我们感觉必须摆脱和逃离。
我们对不同情况会如何反应,就看各个特殊条件的特性而定。如果我们感觉受到威胁,那么我们便会想办法跑开。当恐惧生起,比如说我们总是以想摆脱它来反应,我们想让自己和恐惧离远一点。当然,我们一那样做,我们就更增强了恐惧的力量,赋予它生命。而它将跟著我们,干扰我们,直到我们停止反应为止。
由於当年越战中受伤的结果,我被—种他们称之为「创伤後徵候群」的病症所苦。他们已经为越战的退役军人作过测验,发现很多人因为过去的创伤而引发了这种特殊的焦虑反应。现在对於这个病症已能贴上标签正名当然很好,但是人们却没有办法摆脱它的困扰。从自己过去很多年的经验得知,只要对恐惧一产生抗拒,它就更有力量凌驾我们。而慈悲观的修习对於处理这样的困扰是相当棒的。想去摆脱它们的那种固执减轻了。有个想去和它们作朋友的意愿产生,而明白它们只不过是我们正在经验的一些感受罢了——即使它们在内心中所呈现出的是丑陋、骇人、恐怖的面貌。
好几天来我们已经不断地练习了「愿我自己一切安好,愿其他有情也一切安好。」,或许你已经注意到一种善意、慈悲心的感觉开始生起了。当那种感觉产生了,我们可以放下这个「愿我自己一切安好,愿……」的念头,而更靠近地专注在那些实际的感觉上。然後我们可以更进一步,引导那些感觉向外散发,散发慈悲善意的感觉。「向外」这个字是非常审慎地使用的。一个人可以去体验这种慈爱的感觉——感觉它弥漫十方,感觉我们的世界充满了友善、关切和慈爱的关心。过去那个令人苦恼的,突然间在作慈悲观时就不是。练习一段时间之後,我们对自己的态度便慢慢地会改变。会有更大的耐心和慈悲的自我原谅。以这种方式,慈悲观的修习可以用来当作一种善巧的方法,让我们的心宁静下来和清理、改变我们的一些心态,提供一个更适合的基础来修习内观(Vipassana)——洞见实相的禅修。
当我还待在巴蓬寺时,我和阿姜 连(Ajahn Liam现在是那儿的住持)在一次交谈中,谈到关於修行,他提到慈悲观还是具有某些限制在的。其中一点,我们可能会很容易就变得对它产生执著,因而引发障碍。关於修习慈悲观的利益是决没有问题的,可是有时候人们真的会感觉相当地棒而陶醉其中(执著它):它可以是个非常喜悦和强而有力的经验,不过那并非解脱。它所带来的帮助应该是,接续对于身心的洞见与了知——这是观察内心的练习,是审察探究,是内观(Vipassana)。
因此,这个课程还剩下几天,我想要介绍也许可以称为「智慧因子」的东西。已经练习了几天的慈悲观,我们可以开始来审察探究这个心。目的是为了能看到此时此刻实际正在发生的,看清楚它变化的特性,而明白它无法给予我们处心积虑想寻求的那个满意。我们也明白了另一件事,原来所有正在发生的实相都可以被观察得清清楚楚。这样的明白,对我们而言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看得清清楚楚:它不是我们的。
今晚我想介绍这个「善巧的方法」,而和我们已经在练习的连接起来——只是单纯地问个问题:「谁?」「正在练习慈悲观的那个是谁?此刻正在聆听的那个是谁?那个正在坐著的是谁,谁在疼痛,谁在妄想,谁在困惑,谁在产生疑问,谁在快乐,不快乐的是谁?这是谁?」
作意地带起这个问题「是谁?」,而清楚地注意著心接著的那个状态。心停下来了!我们可以用点力气去发现某些知识层面上的答案:也许在这个空档,我们的名字浮现,也许一个崇高的、似乎更具密意的概念出现,比如说「本心」。只不过「本心」可不是个念头「本心」,「佛性」(佛的觉性)也并非「佛性」这个念头。思惟的念头只是思惟罢了,念头无法真正地回答这个问题:「是谁?」
如果我们不小心,我们使用这个问题「谁?」时,可能只会像一根棍棒或一支猛敲的大锤一样,只是机械式地用来打压任何在心中生起的念头。然而这个练习事实上是要永远保持著一种自我探问的感觉,近乎孩子那种不停歇的好奇心才是。当我们看到孩子不停地探求某种新鲜事物时,我们看到他们那种高兴和好奇好问的样子。像这样的态度用在询问、探究「谁?」的实相上会是相当棒的。
以这种方式,我们可以用在那些干扰我们的东西上面。不安,举个例:「不安是谁?」答案来了:「是我」。那又是谁?「正在走路的是谁?正坐著的是谁?」这种练习可以非常有效地砍除我们的思考、推测和幻想。
然而,从个人的经验中我知道,并非每一个人能够马上利用这个技巧。因此不要觉得我提出来就是要「这样」修行。这是会带来特别利益的一种善巧方法。它的简单明了,是我个人喜欢的。但如果你发现你做不来,或者你觉得似乎没办法完全了解,那么没关系,就回到慈悲观的练习。继续培养那种善意慈悲的感觉,它将会提供你一个合适的气氛来利用这个善巧的方法「是谁?」——如果哪一天你选择利用它的话。
有时候问自己「是谁?」会变得蛮枯躁的——甚至觉得死板而无趣。相反的,慈悲观可以是非常地令人振奋而鼓舞的。将这两种善巧的方法结合起来,对於内观的修行,导致完全的了知与平静——相信会是一个好处方。
*译按:
l、2,3、〔 〕当中,是按经典中的意思略作补充。
4、这个故事中,佛陀的三位阿罗汉弟子:尊者阿那律陀为佛陀十大弟子中天眼第一;尊者难提为乞食耐辱、不避寒暑第一比丘;尊者金毗罗是独处静坐、专意念道第一比丘。
5、加上「不见恶梦」和「诸天守护」,合为修习慈悲观(慈心观)的十一种利益。
伊安·亚当斯(Ian Adams提拉达摩法师)一九四九年生于英属哥伦比亚的新威斯特敏斯特(New Westminster)。在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念工程、地质和地理学时,他暂时中断学业,在中东作了一趟陆路长途旅行;最后他更以一辆单车从巴基斯坦骑到斯里兰卡。他在斯里兰卡的岛屿静居(Island Hermitage)停留两个星期,之后又多待了一个月在堪度波达禅修中心(Kanduboda Meditation Centre)随西瓦利比丘(Bhikkhu Sivoli)练习禅修。
回到加拿大,他完成大学学业,之后他再度到印度去,又前往泰国。一九七三年在泰国出家成为沙弥(samanera)。次年在清迈的明满寺(Wat Meung Man)依通法师(Ven.Tong)受比丘具足戒(upasampada)。
为了向阿姜 查学习,一九七五年他移居到巴蓬寺(Wat Pah Pong)和国际丛林寺院(Wat Pah Nanachat )。他曾在泰国东北和清迈山区作了很多次的行脚(tudong)之旅,向一些有名的森林禅修老师参学。
一九八二年,提拉达摩法师受邀前往英国,帮助那儿的发展。他在戚瑟斯特道场(Chithurst Monastery)待了两年,之后三年负责在诺森伯兰(Northumberland)的汉哈姆精舍(Harnham Vihara)。目前(一九八九),他在瑞士伯恩(Bem)附近的一处新设立的精舍担任资深职事,并且正著手写一本关于戒律(Vinaya——僧侣修道生活的行为规范)的书。
译者按:提拉达摩法师现为瑞士达摩波罗佛法道场(Dhammapala义译为护法)的住持。
修行上的喜悦
底下是一九八八年五月於瑞士,提拉达摩法师在一个十天禅修课程中的第七天所作的开示。开示中提到的「七觉支(觉悟的七个要素)」是:念觉支、择法觉支、精进觉支、喜觉支、轻安觉支、定觉支、舍觉支。
当喜悦产生,正是我们能够发现新事物、更上层楼的时候
……而如果我们已经决定好「生命是苦」,
那么我们就无法更深一层去看清楚。
我们有时候会把修行想错,认为宗教生活是指某种自我鞭笞、自我惩罚。或者,我们通常相信,心灵修习的成果是某种「特殊的」清净。以这样的想法,我们看看自己,当然,怎么看都是不清净的;已经有的——对所谓「觉悟」的概念,我们往自己的心检验看看,看到的刚好都相反——一片纷乱与冲突。
不过重点是,我们对於修行的这些概念「只是」概念。我们想著:「我在这儿,涅盘在那儿;我只是个依然困惑的笨蛋,而涅盘是完全的清净与奥妙。」这样的想法、概念,仅仅是投射在观念上罢了。当我们实际修行时,觉悟是指「实际地」保持觉知在「纷乱、困惑」上。智慧是对愚痴无明的觉知。它不是去知道我们的智慧的一个什么东西,而是「运用」智慧去知道、明白愚痴。
整个念住的修行就是:了解就在此时此处的这个——它的真实特性(实相)。我们不是要去接通某种飘浮在空中的「涅盘的智慧」或者等待智慧落到我们的怀抱中。我们是对人类条件所如实呈现的特性保持著觉知。一旦我们真的明了了如其本然的生命,那么我们就可以开始超越它。如果我们没有真的知道它,就想超越它的话,我们只会陷入错觉当中。
阿姜 查过去常说:「要了解东西有多重之前,我们得先把东西提起来才行。」而当我们知道它们到底多重之後,那么我们就「看见」了苦。看见了苦,我们放下它。当我们放下了它,那么我们就明白它事实上是多么地轻。「哇!多么轻松自在啊!」这就是喜悦生起之处——或者,在「七觉支(七菩提分)」里就称为喜(piti)。
关於「喜(piti)」这个术语有各种不同的翻译。因为有各种的喜悦。昨天我们谈到关於如何藉著苦(dukkha)来刺激、引发我们去寻求「正道」的动机,我们因而产生了信任——而这种信任接著就带来喜悦。
因此,在修行当中,我们有各种因为不同原因而有的喜悦生起,而且个人来说,我发现思惟它们非常有用。当我们谈到关於心灵上的训练时,喜悦的重点和它的作用似乎常常会被忽略。
喜(piti)不是只是一种美好时光的快乐,而是一种能够敞开生命、导向觉醒的经验。当喜悦产生,正是我们能够发现新事物、更上层楼的时候;另一方面来说,如果我们已经决定好「生命是苦」,判定它就是「悲惨的」,那么我们就无法更深一层去看清楚。
想—想小孩子:注意—下他们是如何地观察和想要去发现——他们纯真的对於事物的著迷。可悲的是,身为大人的我们,已经变得太过世故、复杂,绕著花花草草等等这些小事情团团转。我们老是忙於概念层面上太多。当我们看见一朵花,我们心里知道「花」,然後,「是的,我对於花清楚得很,一生中我已看过太多,而这只是另一种『花』罢了。」但事实上,每一朵花都是独一无二的;它是在这儿、在此刻、现在、这个地方的这朵花。
如果我们能够真正地倾听,比如说,倾听一只鸟儿歌唱;就只有声音。那是完全不同於思惟:「噢,另一只鸟儿在唱歌」。如果我们「真实地」倾听,就在此刻、在这个地方、在这种情境下,单纯地只有声音呈现著;而且,有一个知道的倾听本身。那么,这是和思惟著「鸟儿歌唱」完完全全不同的实相。
如果我们总是掉回到概念的层面,那么内心的对话就会喋喋不休:「小鸟儿在唱歌。花在那儿。这个人在讲话。我希望他们安静下来。蜡烛在燃烧……等等。」而我们却认为我们对生命全然知晓!我们在头脑里不断地变这些概念的戏法,怎么变还不都只是从脑子的这一边跑到那一边——在脑子里,无非是从记忆转为言辞表达,然後再回到记忆,如此而已。如果我们只住在生命的概念当中,它可以变得无聊透顶——老是这些相同的字眼——「花,鸟,树」。
我们经由语言来学习和了解,也透过语言来表达我们的了解,那么很自然的,我们当中的许多人就成了语言的囚犯。藉著禅修,现在我们有了机会,在我们的西方文明中带来一个深切的改变。我们正试著在一个「非概念式」的层面上去了解。在禅修当中,我们直接地明白经验的实相。
完全认同言语表达的人们可能会觉得上面这样说太吓人,但我们总是不想讲些拐弯抹角的话;我们仍然必须表达自己;我们仍然需要传达出来。不过我们应该认清一个事实:沟通上所使用的言语和我们尝试传达出来的这种「经验」是不同的。
在我们的社会中,给了「静默」太少空间。近日,言语已经变得如此大声、如此地具有影响力,有时候我们所听到的全是这些。不过,仅有的一点静默空间,还是给了我们门路、训练培育的机会和另一种表达方式。再一次能回复到像一个纯真的孩子一样,并且不为言语所限,多么棒啊!
刚开始,孩于们对花儿没有言语的称呼。「这是什么呢?」孩子问。我们告诉他们:「这是一朵花」。好,这没关系,因为他们必须学习沟通;不过呢,也许我们应该试著表达:「嗯,人们叫它『花』,但这并非它的真实面目。它有属於自己的完美特性,就是它如实呈现出来的那个样子——只是如其本然罢了。」明白这个「只是如其本然」,就是明白喜悦。所谓明白喜悦就是指,能把许多已从我们生命中流失的那些美丽的特质给带回来。现在我们有了一把秘密的钥匙,会帮助我们从自己的习性当中解脱出来。
喜悦的特质也可以再更上发展。超越喜(piti)——心灵的喜悦,有个更稳固的特质称为乐(sukha)。通常,sukha 乐这个字只翻译成快乐——苦(dukkha)的相反——但这是不够的。瞬间的快乐就像一只蝴蝶四处飞舞、翩翩而过。这当然很好,不过还不是sukha乐所指的那种深切的幸福安乐。生活在这么多的概念当中,我们的生活变得无聊,而一些转瞬即逝的刺激、乐事纷纷出炉,在我们身边变得重要起来(这是一般生活中短暂的快乐,并非这里所指的「乐」(sukha)))。
乐(sukha),另一方面来说,意思是说:「一切都美好。」它是周遍身心的一种宁静和幸福的感觉。它使得心安样、专注而镇定,给「定」(samadhi)提供了一个坚固的基础。
回到喜悦来说:喜悦是时间到了自然会产生的。你没有办法预想它,你无法造作出它来。它只在该来的时刻生起。真正的喜悦生起的时候,你便真正是活在当下。因此这样的喜悦,对我们而言成了一个很有价值的参考点:如果有了真正的喜悦,那么我们知道我们是「在」当下;如果我们是真正地活在当下,那么就会有真正的喜悦。
因此,试著去探索喜悦从哪儿来。看看是什么帮助它能生起和什么让它消逝。当我们这样去做,我们就开始在培养这个「七觉支」当中的「喜悦」。在引领我们走向觉悟的所有特质当中(七觉支),它成为其中一个。
维陶特斯·阿克尔斯(Vitauts Akers维拉达摩法师)一九四七年生于德国的厄斯林卷(Esslingen),父母是拉脱维亚(Latvian)难民。五岁时,全家搬到加拿大多伦多去。他在多伦多大学念工程学,但是随著他对学校生活的幻想破灭,他选择辍学离开(一九六九年),前往德国工作。之后,当他待在印度时,遭遇佛法,遇见已故的菩提沙考法师(Samanera Bodhesako)介绍了若那维拉长老(Ven.Nanavira Thera)著作给他看。最后,他前往泰国出家,在摩诃塔特寺(Wat Mahathat)剃度成为沙弥(samanera)一九七四年在巴蓬寺(Wat Pah Pong)受比丘具足戒(upasampada)。法师是国际丛林寺院(Wat Pah Nanachat)的首批住众之一。
在泰国住了四年,一九七七年法师回加拿大和德国探望家人。之后,在阿姜 查的要求下,法师加入阿姜 苏美多在伦敦的汉普斯特精舍(Hampstead Vihara),而没回去泰国。往后几年,他投入了戚瑟斯特(Chithurst)和汉哈姆(Harnham)两处道场建立工作上。
一九八五年,受威灵顿南博(上座部)佛教协会(Wellington Theravada Buddhist Association)的邀请,他移驻纽西兰,塔那瓦罗法师(Ven.Thanavaro)与之同行。最初,他们住在威灵顿市区,两年后移到二十九公里外史托克斯山谷一块四十三英亩的土地上。这个道场由阿姜 苏美多取名为“菩提若那拉玛”(Bodhinyanarama);一九八九年,阿姜 苏美多并亲自主持了在那儿首次的比丘具足戒仪式。
维拉达摩法师从事各种教学活动不遗余力,也包括每个月前往在奥克兰已然建立的一处精舍。偶尔,他也到南岛(South Island)弘法教学。
译者按:法师目前住在菩提若那拉玛道场(Bodhinyanarama Monastery)。
又如何
底下这篇关於「四圣谛」的教导,是维拉达摩法师於一九八八年六月在泰国曼谷为当地居士们所主持的十日禅修课程中所作的一篇开示。
这个教导的目标,并非只是「得到」另一种特殊经验……
而是在任何经验当中,完全的解脱。
今天晚上,我们来思惟一下佛陀一生的传说。现在,我们可以把这个故事当作真实的历史;或者,我们也可以将之视为只是一种神话——用来返照自己在寻求真理上发展的一个故事。
故事中,话说在他成就觉悟之前,菩萨(成佛之前)住在王族当中,他具有很大的权力和影响力。他天赋异秉,拥有了任何人都羡慕的—切:财富、聪明才智、魅力、英挺庄严、友谊、为人恭敬、和许多技能。他过著奢华舒适、无忧无虑的太子生活。
传说中,当菩萨降生,净饭王接收到来自智者的预言,他们说有两个可能:他的儿子将成为转轮圣王;或者,是成为一位完全觉悟的佛陀,父王当然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继承王位,可不想让他出家遁世。因此皇宫中每个人都竭尽所能地保护太子。有人衰老了或者病了,就被带走;大家都不希望太子看到任何不快意、可能导致他出走的事。
二十九岁那年,好奇心兴起,太子想看看外面的世界像什么样子,於是他和他的车匿(车夫)出宫去——他看到了什么?首先看到的是个生病的人——满身是疮,在痛苦中哀嚎,躺在自身的秽物当中。一个彻底悲惨的人类境况。
「那是什么?」太子问他的侍从。车匿回答:「那是一个病人」。一段谈话之後,太子第一次了解,人类的身体是会生病和变得这般痛苦的。车匿指出所有人的身体都潜具这种可能。对太子来说,这是天大的震撼。
隔天他又出了皇宫。这一次他看到一位老人:老态龙钟,行步俛偻,颤动的身子,满是皱纹,灰白的头发,气力衰弱地只能勉强支撑住自己的身子。同样地,内心为之一震,太子问道:「那是什么?」。「那是个老人」车匿回答,他接著说:「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因此太子明白这个身体也具有变为衰老的本质。见到这一幕,太子整个人楞住了,回到了宫中。
第三次出宫,看到了死人。大部分城里的居民是忙碌的,高兴地向他们的太子挥手致意,心想太子必然会有一段快乐时光。无奈人群的後面,有人以担架抬著一具尸体,往火葬场而去。这对太子又是强有力的一击,「那是什么呢?!」他问。车匿回答:「那是一具尸体,每一个人最终都是如此;你,我,他们,都一样要死去。」这真是个不小的震撼。
接下来再一次,菩萨(太子)出宫去,看到了一位托钵僧——坐在一棵树下静默禅修。「那是谁?」他问。车匿回答:「那是出家僧侣(sadhu)——他们正在寻求生命和死亡的答案。」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佛陀的传说。这对你我到底有何意义?它只是个可以向孩子们说的历史故事,一个关於有个人二十九岁之前连老、病或死都没看过的一则故事,是吗?
对我而言,这个故事所传达的,是对於感官经验的有限——一个人类心灵的觉醒。想起自己当年在念大学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对生命产生很多疑问:「生命到底是什么?」「它到头来往哪儿去?」我总是会想到死亡,而开始妄想:「拿到大学毕业文凭是为了什么?即使我成为—个有名的工程师,或者变为富有,我还是逐渐步向死亡。如果我成为最棒的政治家,最佳的律师,或无论最好的什么……即使我成为史上最为出名的摇滚明星……又怎么样?」当时,我认为吉米·韩德里克斯(译按:当时在美国的一位知名摇滚歌手)就是吸食太多的海洛因而死的。
当然,那时所想的,都没能回答关於死亡的问题。而我总是想著:「又如何?……如果我有了家庭,如果我很有名气,如果我不为人知,如果我有很多钱,如果我没有很多钱……又如何?」这些还不是一样都无法解答疑问:「死亡到底是什么?为何我在这儿?为什么要去寻求某种经验,如果终归要死亡的话?」
像这样不停地问自己,自己根本不可能再念书念得下去。因此我开始旅行。我以旅行来暂时转移自己的注意力,因为旅行是有趣的:摩洛哥、土耳其、印度……。但是,我还是再度回到了相同的结论:「又如何?如果我参观了另—个寺庙,如果我看了另一个回教的圣殿,如果我尝过了另一种食物——又如何?」
有时候,当人们听到死亡,或者他们生病了、老了,或者来自於宗教上的洞察,这些疑问便会生起。心里面喀搭一声,我们对於事实真相的觉醒:无论我们有了什么经验,它们都会改变,都会结束,都将逝去。即使我是世界上最出名、最有权力、最富有、最有影响力的人,所有这些终将死去。它将会消失。因此,「又如何?」这个疑问,是心的一个觉醒。
如果我们来参加十天的禅修课程是抱著想得到「某种禅修经验」的想法,那么「又如何?」我们依然得回去工作,依然得面对这个世界,依然必须回到墨尔本,回到纽西兰……又如何!「一种禅修经验」和「一趟皇后伊莉莎白二号海上之旅」有什么不同呢?也许便宜些吧!
佛陀教导的目标,并非只是「得到」另一种特殊经验。而是关於对经验本身的特性、真实相的一种了解。目标在於真实地观察身为一个人类有情的意义何在。我们正在看清楚生命,正在放下幻觉,放下人类痛苦的根源,明了实相,明了「法」。而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过程。
当我们练习「对呼吸的念住」——anapana sati——我们不是要藉著这个努力,稍後来得到什么。我们练习对呼吸的觉知,单纯地就只是念住在当下所发生的:就只是念住在进来的气息上,念住在出去的气息上。那么,当我们不断地保持像这样的念住,会有什么结果呢?嗯,我想我们都可以看得到的,心宁静下来了,我们的注意力稳定下来了——我们保持著觉知,并与事物如实呈现的实相同在。
因此,我们已经能够明白,让心宁静下来是一件对我们自己健康有益而慈悲的事。而且,也注意到了,这样的练习在心中创造了更多空间。我们可以看到,此刻真的能「保持专注」在生命上——的这种潜能。我们的注意力不再被牵动不息,我们不再老是「被绑架」。我们能真正地与专注力同在。
如果我们被某件事所困扰,我们整个注意力都会被吸引,而萦绕在这个扰人的事物上。当我们担心忧虑、筋疲力竭、心烦意乱、兴奋、渴求、沮丧……等等,我们的专注能量便失去了。因此,藉著使心宁静下来,我们创造了空间,让专注力得以「解脱」出来。
这时候,会有一种美好的感觉。当我们在一段禅修之後走到外边,也许我们会以一种全新的心态注意到事物——浓绿的树木、扑鼻的清香、走在小径上、盛开的莲花。这些令人愉悦的经验使得我们宁静、放松下来,这非常有帮助——如同作了一趟海上航行一般。在纽西兰,他们喜欢以在山中健行的方式放松自己。
但是这种快乐(sukha),还不完全是佛陀的特质。这个层次的修行可以引发很多的喜悦,但还不够。这种相对宁静的心的快乐,并不是完全的解脱。这仍然只是另一种经验,它仍旧含括在「又如何!」当中。
佛陀完全的解脱来自於对内外诸法的探究——dhammavicaya(对於法的审察——择法)。它是冲突和紧张完全地终结。无论生命中我们在哪儿、处於何种境况,都不再有问题与麻烦。这称为「如如不动的心的解脱」——在任何经验当中,完全的解脱。
关於这条正道的诸多美好当中,其中有一个特质是:它可以应用在所有的境况当中。我们不一定非得在道场里,或者要有快乐的感觉,才能够思惟正法。我们可以在痛苦当中思惟(观察)法。我们经常会发现,人们总是受苦时才会想到到道场里来;当他们快乐、他们诸事顺利时,就不可能发生。如果他们的另一半离家,或者他们丢了工作,得癌症什么的,那么他们才会说:「噢,我现在该怎么做呢?」
因此对我们当中的许多人而言,佛陀的教导就从痛苦(dukkha)的经验开始。这就是我们开始用心思惟与观察的。过些时候,我们发现我们也需要思惟(观察)快乐(sukha)。不过呢,人们开始的时候,不会是去见老师,说:「噢,敬爱的师父,我这么快乐,帮帮我,让我远离快乐吧!」
通常,当生命说:「受伤害、受苦了」,我们才开始。也许它只是个厌倦的感觉;但对我而言,它是对死亡的思惟——一切都是「又如何?」。也许它是对工作的一种倦怠感;在西方,我们称之为「中年危机」;人们到了大约四十五岁或五十岁时,开始会想:「我该有的都有了」或「我什么也没成就,又如何?」「又怎么样呢?」某个东西醒觉过来,我们开始质疑生命。无论在粗或细的层面上,每—个人都会经验到苦(dukkha)的;而佛陀的教导就是从这儿开始的,多么美好啊!佛陀说:「存在著『苦』(苦谛)」,没有人可以否认这个事实。佛法的教导便是由此建立起来的——如实地观察这些我们有的种种经验——观察生命。
面对苦(dukkha),世俗的方式便是试著去摆脱它。通常我们运用我们的聪明,试著去尽可能地取乐(sukha)和竭尽所能地避免痛苦(dukkha)。我们总是千方百计要让一切更加方便、一切如己所愿。我记得我的老师(Luang Por 阿姜 查),有一次相关的开示。
当时在泰国的道场里,我们经常得一块儿从井里打水。一根长长的竹扁担,中间两桶水,两头各一个僧人合力挑著。有一次阿姜 查说:「为什么你们老是和自己喜欢的人一起挑水呢?你应该和你不喜欢的人一起挑水才对!」这话真是一针见血。我当时是个动作非常快的沙弥,我总是想办法避免让动作慢的老比丘在扁担的前端和我一起挑水。因为这会让我受不了。有时候避免不了碰上了,老比丘在我前头一起挑水,他动作慢、碍著我了,挑著挑著我还一直在扁担上使力推促著他走……。
因此,必须和一个我不喜欢的人一起挑水是苦(dukkha)。而如阿姜 查所说的,我总是想办法让事物如己所愿地呈现;总是运用聪明试著去得到最大的乐和把苦减到最低。不过,即使我们得到了自己想要的,我们仍旧有「苦」;因为满足的喜悦不是永恒的——它是无常的(anicca)。你可以想像,吃著某种美味佳肴,开始时当然觉得愉悦;但如果你必须吃它四个小时,它就要变得可怕。
面对苦(dukkha),我们做些什么呢?佛法的教导说:运用智慧,真正地看著它。那就是为什么,我们把自己丢到像这样的一个禅修课程当中,还受持八戒。我们是真的看著「苦」,而不是竭尽所能地取「乐」。寺院修道的生活便是立基於此;我们似乎为僧衣和袈裟所限,但我们却能有一个难以置信的自在心态来看著痛苦——而不是无知地只想摆脱掉它。
在西方,穿著这袭袈裟可真的是困难。它可不像在泰国一样平常。我第一次来到伦敦时,觉得非常格格不入。就算自己还在家时,我都避免穿得引人注目了;更何况此时,这么地无所遁形。对我来说这是苦,我感觉很不自在。人们老是盯著我看。如果我可以自由地尽可能取「乐」和避免「苦」的话,我一定穿上牛仔裤,咖啡色衬衫,留撮胡子,淹没在熙来攘往的人群当中。当然,我不会那样做,因为我已然舍俗、出家受戒。况且,舍俗(舍离)的真正意义是指放弃了原本的习性——放弃了总是竭尽所能抓取愉悦、快乐的那种习性。在当时那种情况,我的确学习到很多。
我们都各有各的责任:家庭、工作、职业……等等。这些是各种的限制,是吗?面对这些情况我们怎么做呢?与其怨叹这些限制:「噢,要是情况不这样,我一定会很快乐的」,我们可以这样思惟:「现在正是去明了真相的大好机会」,我们说:「这就是当下如其本然的实相,这是苦(dukkha)。」我们实际地迎向痛苦(dukkha);我们觉知著苦——将它带至心中。我们不用特别再去创造「苦」,这个世间早已存在了足够的痛苦。而佛法的教导鼓励我们去真实地感觉存在我们生命中的苦(dukkha)。
也许在这个课程中,禅坐时你会觉得厌烦、不安,老是盼著敲钟开静。现在你能够真实地注意到了,如果没有这样的时间安排,我们可能早就走出禅堂了。而如果,我带著不安定出禅堂,会发生什么事呢?我可能心里想著,嗯,我已经摆脱不安了,但实际是这样吗?我离开了,去看看电视或阅读个什么——我还是带著不安。我发现自己的心并非平静,充满各种活动。为什么呢?因为我已随著「乐」走,而老是想摆脱「苦」(dukkha)。那是不停歇的,痛苦的,我们生命中的不安。它是那么地不令人满意,那么地不平静——离涅盘太远。
佛法教导中的第一个圣谛并不是说:「得到这个经验」;而是说:看著苦的经验。我们不应该只是对佛法的相信——只把它当作「教导」;而是要看清楚「苦」——没有任何喜不喜欢的判断。我们不说:「我不该有苦」;也不仅仅只是「想著」苦。我们正实际地感觉著它——观察著它。我们正将它带到心中。因此第一个圣谛是:苦谛。
继续这个教导,我们知道苦有其原因,而且苦有个结束(止息)。很多西方人认为佛法是非常消极的教导,因为它老是谈论关於「痛苦」。从前,我第一次得到启示很想出家成为佛门僧侣,是在印度。当时正巧我的祖父过世,我回到德国参加葬礼。我试著告诉母亲关於剃度的事。当我提到「苦」,她变得非常难过,她太过於掉入自己的想法。母亲并不了解我所说的:其实这是个再单纯不过的事实——人类都必须经历过的。
佛陀并不是只谈到「苦」,他也谈到关於苦的生起原因、苦的止息和达到苦的止息的道路。这整个教导便是关於觉悟——涅盘。而这就是这个佛陀的形像所述说的意义。它不是佛陀苦的形像,而是觉悟的形像,是解脱这回事。
要达到觉悟,我们必须接受我们所碰上的,而不是试著去得到我们所想要的。以一般世俗的方式,我们经常想法子得到我们想要的。我们都想要涅盘——是吗?——即使我们并不知道那是什么。当我们肚子饿了,我们到冰箱里拿些东西,或者上市场去买些东西。拿取,拿取,总是想得到个什么东西……但是如果我们以这种方式想得到(抓取)觉悟,是行不通的。如果我们可以像得到钱、得到车子一样,得到觉悟的话,这还多少容易—些。可是,觉悟远比这些微细得多。它需要智慧(panna),它需要对诸法实相的审察探究,dhammavicaya。
因此现在我们正运用著智慧,不去竭尽所能地取「乐」(sukha)和避「苦」(dukkha),而只是实际地看著苦(dukkha)。我们先善巧地作些思惟,「为什么我正受著苦?」。你明白,此时我们并不摒除思惟,思惟是个非常重要的工具。如果我们不思惟得清楚些,根本不可能真正地实践佛法的教导。
当然,你也不需要成为通晓佛学的博士。佛法中的智慧并非只是一些概念的累积——经验要比佛学知识来得更为重要;智慧是建立在体验上的。
智慧是观察生命和询问正确问题的能力。我们正在运用思惟,将心导入正途。我们对於所发生的状况,正以一种开放的心灵接受著它并且观察著它。以这种放开的心,这种正确的疑情,我们所练习的正是内观(Vipassana):洞见我们如实呈现的实相。心正带著佛法教导的观念,而将智慧导向人类的实际体验。我们是开阔的,专注的,明了事物如其本然的实相。这种对四圣谛的探究,正是在佛法中典型的智慧的应用。
因此,单纯地就只是观察著苦(dukkha),不是试图去得到一种什么经验。对於我们的苦——我们内在的冲突,我们的责任便是接受。我们感觉到内在的冲突——我正受著苦。然後我们问:「什么是产生的原因?」
佛法的教导告诉我们,苦开始而後结束——它不是永恒存在的,它是无常的。假设打坐时我感觉到不舒服,我转向那个苦,问自己:「产生这个苦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现在身体坐得不舒服嘛。」——答案来了。於是我决定移动身体。但过了五分钟,我发现身体又不舒服了。因此这一次,我就更靠近一点看著这种感觉;我注意到事实更多一些:「事实上,是因为我不想要不舒服,我想要愉悦的感受。」啊!真正的问题不在於疼痛的感受,而是那个「不想要苦受」的家伙。现在,这样的洞见就非常有用了,不是吗?这是稍微深层一点的了解。我发现,现在自己更能平静、平稳地看著苦受而可以不去移动了。没有不安,心变得十分宁静。
我已然看到问题(麻烦)的原因并不是苦受本身,而是「不想要」那种特别的感受。「想要」是个非常狡猾的家伙,它以各种面貌出现。我们可以始终应用相同的问题问自己:「此刻我『想要』什么?」。第二个圣谛——苦的起源(samudaya 集谛)——苦的起因就是对「想要」的执著——tanha(渴爱、贪欲)。它使得我们感觉,如果我们得到我们所想要的,我们便能得到满足:「如果我有这个」、「如果我成为那个」,或者「如果我能摆脱这个;如果没有那个」……而那正是生死轮回(samsara)的不断流转。欲爱和恐惧,总是推著有情轮转於「有」中;总是寻求出生,导致忙碌不息、无止尽的生命迁流。
佛陀说有个「出离的方法」,有个苦的止息。苦的止息,我们称之为涅盘——灭。当我第一次读到关於涅盘,我知道它是指没有贪、没有嗔、没有痴。因此我想,只要能够「摆脱掉」贪、嗔和痴,那么那就是涅盘了——似乎是如此。我尝试了却行不通,我更加困惑。
但是当我继续修行下去,我发现「苦的止息」是指:该结束的时候,这些事物便会结束——它们有它们自己的能量。我无法告诉自己:「好的,明天我将不贪婪,我将不害怕。」这是个荒谬的想法。我们必须做的是,去「包容」这些能量直到它们死去——直到它们停止。如果我觉得生气而有所反应,也许我会一脚踢去,踢到某人的小腿上,然後他们回踢我一脚,之後,我们就打起来了。或者,我回到自己的寮房禅修,坐在那儿憎恨我自己、对自己生气。情况继续不停地演变下去,因为我已经对所发生的事物习性地反应了。如果我顺著习性反应或者试著要摆脱、压抑,那么愈演愈烈的情况就不会中止。这把火就不会熄灭。
四圣谛的教导是:我们有苦(dukkha):苦有个起因(集samudaya);苦有止息(灭 nirodha);以及通往灭苦的道路(道magga)这是个多么实际的教导啊!在任何内在冲突的状况下,我们可以将所感受到的:「为什么我正受著苦?我此刻想要的是什么?」——作为自己的责任来探究清楚。我们可以去审察抉择诸法的实相(dhammavicaya 择法)。
很重要的是,我们得实际地应用这些教导。阿姜 查以前常说:「有时候,人们非常亲近佛法,就像蚂蚁爬满了芒果的外皮,他们却从来没有真正地尝到果汁的滋味。」有时候,我们听闻了这些教导的轮廓,而认为自己都了解了:「那只不过是一种观察生命的方式嘛!」但事实上,这些教导并不只是一种知识层面(意识层面)上的结构而已;而是清楚地昭示,「经验」本身有其结构(意义),我们得明了它才行。
因此,不能只是运用聪明来竭尽所能地取「乐」、避「苦」;我们要运用智慧来让心解脱,来超越,来明白我们的心如如不动的自在,体证涅盘。我们运用智慧是为了自在无碍,而非只是浪荡轻浮;心能解脱、无恼,而非只是表面的快乐。我们正在超越快乐与不快乐。这和只是努力地想去得到某种经验——和这样的心态是不同的。
这是今晚留给大家思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