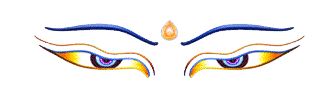比丘圆真的前世
珠古•努•巴杂冉那 随记
2006.元月6日 15:40
写在前面的话——缘起
认识圆真是西历一九九八年仲夏时节的事。
那日我正在小闭关房中做大幻化寂忿本尊的修习。山上的桂子花有的已经开了,散发着淡淡的馨香,山脚是奔腾不息的江水。日近黄昏,太阳的余辉从木窗格子里透出来,撒在我的卡垫上,我正做着戳哇(忿怒五十八尊)的观修和诵念。坛城中忽然多了一抹身影,鼻腔中钻入一股雪山上雪莲花的香味,清冽、甘苦、倔拗。他慢慢的向我靠近,我凝神定眼望向他时,他就伫立在法结界的内缘,是个相貌奇美的男孩,面如温玉,秀眉朗目,让我有一种说不出的熟悉。
“是因为雪莲花还是阿尼玛青雪山?”我问自己。
他时而身着袈裟,时而身穿喇嘛服,时而身着各式法衣。
“停!不许再换来换去的变衣服!”我眼都花了。
“您所见,皆是我的本生。”他淡定道。
“我又有奇闻可听了。”我高兴的说。这就是闭关时最大的乐趣。
“不。”他回绝了,“我是来请求您送我到东方不动佛土的。”
“好吧。”执起铃杵,弹弹手指,他已经去到了他喜欢的地方了。
而我也没啥记得。每日有如此多的新生及过往亡灵要去往他们的地方,数不过来,反正这是功课的一部分。
八年后,冬至。
南方的冬天还是很暖,修完最后一座法,夜已经很深了。净过身,我躺下修风息,鼻子里钻来一股清甘、冰香的味道。
“小僧比丘,往昔名作圆真,又做土登尼玛。烦请尊者听我一述我昔本生之事,以励后世之人。”
以下便是我所记录的比丘圆真历劫生死的修行生活中的点滴,无有增添,只因所涉佛法密部相关法要时,而略作删减。
一、大唐往事
第一集:钟声
我躺着,看见远远连绵大唐国土的山脉,葱茏万里,一直连着我的家乡星罗国。
我的眼睛升起一片薄薄的白雾,我的身体是麻木的,我知道我的灵魂开始慢慢的剥离这个肉体,就象剥桔皮似的一瓣一瓣的,体内以前那活泼的象小溪流的血液在一阵一阵的痉挛。
我右肩至后背的刀伤让我再也回不到家乡。挂在胸前的护身符传来我熟悉的檀香味,那是白马寺的味道,是云檀法师亲手挂在我项上的。我执意要跟随商队返家乡,可是在这个秋季在这条官道上我们遇劫了,我现在感觉自己好重,好沉,就象背着百来斤的粮包去给山上的师兄送粮食一样,压得我喘不过气。我的嘴巴一张一翕,一定象极了放生河里快死的鱼,不知道那些鱼儿快死的时候想什么,可是我却能清楚的知道自己的一切。哎,我才不想死掉,我从大唐京都各大禅院带来满满一马车的各类经典、论著还没有护送回家乡——我的寺院天雪寺。
天雪寺位于天雪山的山腰上,山顶是终年积雪,而山下却有看不完的四季幻影。我现在开始想念天雪山上的雪莲花,大印法师说我是天雪山雪莲花的花神转生,是佛根具足的佛弟子。只是这会儿身为授足比丘戒律的我圆真,在这临死的当口却不能一心口诵佛号,心观佛形,顺顺当当的往生极乐佛土,平素这一心不乱、只习佛经的脑袋却竟想着和往生不搭界的事情,从小师傅就说过往生之时应当如何忆念佛,心不散逸,免堕恶趣……一声闷哼,令我头晕眼黑,四周黑咕隆咚,我到底死了吗?我自己都不敢确定,但是我的身体确实无法动弹,唯一能动的就是这如脱缰野马的脑袋,收都收不回。完了,我一定会堕入恶趣,“恶趣”这个念头一闪现我就觉得往下沉,是进入地狱了吗?我很绝望,因为我紧张,全身上下绷的紧紧的,我在痉挛,很疼,喉咙在收缩,“水”,我想喝水,我很渴,身上的血和体液好象都蒸发干了一样,(水,对于临死之人很重要,他在亡灵意识不清的时候能够保持清醒,不至在中阴期误食不洁饮食,而昏欲堕恶趣傍生,或受香触、味觉的诱惑而投贫贱人家。)我想起来,这是游学中州西京寺参学华严十地讲法时,西京寺的主事大和尚隆严法师所讲的。
当时西京寺附近有一户胡姓施主,他是西京寺的常香客,大施主。我去寺院时正值胡施主家一年旬90的老翁仙逝,想请寺院做布萨超度法事。法事的日子选在老翁逝去的第3天。在这前几日,老翁的长子胡老爷——一年约70有余的精瘦老者就前来和隆严法师在厢房中商议此事,我随待在旁。抬眼望去这位胡老爷身着黑缎锦服,身形削长,两肩却很宽,看起来身子很硬实,尤其是双眼眼窝很深,眼珠似黑又似青,眼白却很少,鼻梁坚挺,从侧面看上去象刀削一样,两唇很薄但很长,蓄着稀疏的胡子,“精明、严肃、刻板”是我对他的印象。“估计是个官场人”,我开始评估了。他伸出修长枯瘦的双手端起茶碗呷了一口,两眼皮也不抬的就说道:“法师,烦请您选定日子时辰,我届时会率家中老幼前往大殿敬香聆法,所需费用我先奉上800纹银,十担大米,十担面粉,三车应季时蔬瓜果,百斤灯油,
2006.元月7日 15:19
50担木柴,若还需什么,尽请知会我府上管事,也尽人子之力咧!连同施斋日也请法师一并代劳,我先在此谢过了。”清清朗朗的话音一落,隆严法师脸上掠过一丝肃容,立即接过:“施主赤诚之心,老衲岂会不知。请胡施主安心便是了。”说完就是一副要送客的样子。这位胡老爷当真是知得人事,起身,捻根香燃后敬在侧身供奉的弥勒佛前的香炉上,拜了一拜,便向隆严法师合十告退了。
我当真是看的一头雾水。这位胡老爷端着架子,看不出丝毫的悲伤,反正家中的老父也是高寿归西的人,倒也伤心不到哪里去。只是隆严法师可不同,我参学西京寺在隆严法师座下听授已两月有余,法师可是心性纯净,语言风趣得很,常在讲学之时引些民俗掌故消化枯燥繁冗的经论。我很喜欢在他老人家坐下听课,他很象我天雪寺的大印法师,很是让人容易亲近,最好笑的是他脸上圆圆的大鼻头,笑起来时鱼尾纹一直延伸到耳朵的上方,肥胖而粗短的十指永远都重复一个动作——拨动着乌黑油亮甚至泛着红光的檀木念珠。他的个子偏偏又长的奇高,穿上宽大的袈裟更像是是一堵活动的墙。每日早晨五更时分不到他就会在大殿上撞击那口青铜大钟,“咚……咣……”沉闷的钟声就会从寺院里穿墙而出,漫延在这个小镇的每个角落。
(待续) |
 发表于 2006-1-9 01:01
发表于 2006-1-9 01:01
 发表于 2006-1-10 11:43
发表于 2006-1-10 11:43
 发表于 2006-1-11 17:43
发表于 2006-1-11 17:43
 发表于 2006-1-13 14:14
发表于 2006-1-13 14:14
 发表于 2006-1-16 17:29
发表于 2006-1-16 17:29
 发表于 2006-1-21 00:45
发表于 2006-1-21 00:45
 发表于 2006-1-24 21:49
发表于 2006-1-24 21:49
 发表于 2006-1-27 00:43
发表于 2006-1-27 00:43
 发表于 2006-2-1 03:20
发表于 2006-2-1 03:20
 发表于 2006-2-2 02:53
发表于 2006-2-2 02:53
 发表于 2006-2-6 00:46
发表于 2006-2-6 00:46
 发表于 2006-2-21 00:04
发表于 2006-2-21 00:04
 发表于 2006-6-3 20:31
发表于 2006-6-3 20:31
 发表于 2009-1-15 15:16
发表于 2009-1-15 15:16
 发表于 2009-12-10 18:04
发表于 2009-12-10 18:04
 发表于 2010-10-24 01:20
发表于 2010-10-24 01:20
 发表于 2010-10-24 01:20
发表于 2010-10-24 01:20
 发表于 2010-10-24 01:21
发表于 2010-10-24 01:21
 发表于 2010-12-6 20:54
发表于 2010-12-6 20: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