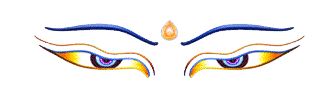西藏西部艺术的绝响
佛的世界
在古格故城的所有遗迹、遗物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一大批保存至今的佛教艺术品了。佛殿、佛窟中绘满墙壁的精采壁画,殿顶五彩缤纷的天花板图案,刻在卵石表面的佛与菩萨,模制在小泥片上的各种造像,精心雕凿的门楣、门框、柱头,这一切全面展示了古格人对佛教的虔诚信仰和对艺术创作的执着追求,也给我们留下了一个研究古格王国历史、宗教、文化的横切面。
在我们1985年去阿里考察之前,已经有一批西藏的艺术家到过古格故城。这些西藏艺术的寻宝者曾经探访过西藏各地的许多寺院,看到过大量不同风格的壁画、塑像、金铜造像、唐卡(西藏式的卷轴佛画)。但他们一走进古格故城的佛殿,立刻就被这里风格独特、色彩艳丽的壁画和天花彩绘给吸引住了。欣喜若狂之余,不假思索地喻之为“古格流派”。
我们初到古格故城时也是同样的感觉,但我们在欣喜兴奋之后考虑得更多的是,怎样使这批艺术珍品变成完整的资料,怎么样找到研究它的钥匙。为此我们把半数以上的人员和大量的时间投入到对壁画、天花彩绘、雕塑的调查之中。拍摄每一幅画面、每一个图案、每一件雕塑,抄录每一条藏文题记,记录、测量、临摹,认真观察,仔细揣摩,一遍又一遍地品味,每天都有许多新的发现和新的体会。
为了避免灯光和自然光混杂而影响图像的色调,考察队的摄影师和录像人员连续干了20多个夜晚;为了保证测量数据的准确和抄录藏文题记的无误,我们整天搬着独木梯爬上爬下,最终形成了一套科学完整的记录资料。
庄严威猛娇媚
壁画是古格艺术的大宗。古格风格的壁画整体布局严谨规整,通常以绘制的大像或塑像背光为主体,四周或两侧排列相关的许多小像。佛传故事画多呈分幅长卷式或分幅组合式,礼佛、庆典乐舞、商旅运输等内容则多为单幅长卷或组合长卷式。佛界人物造型在遵守造像度量程式的前提下尽可能表现出丰富的神情、姿态,少有僵化呆板之感。特别是在绘制佛母、度母、神母、供养天女等题材的造像中,创造出一种身材修长、隆乳丰臀、腰肢婀娜、容貌娇好的美女形象。
其中裸体的供养天女、空行母、神母可以被看作是西藏壁画中最优美的人体造型。古格壁画中的世俗人物形象似乎没有形成明显的严格程式规范,除王统图和礼佛图中的王室成员外,其他人物多为画匠的即兴之作。相貌、神情、动作等变化多端,服饰、用具也丰富多彩,反映的内容有礼佛、鼓乐、舞蹈、杂技、商旅运输、贡奉等许多方面,完全是古格王国时期现实生活的写照。
在调查时我们特别注意观察了几处受到不同程度破坏的壁画,发现古格故城的壁画都绘在1-1.5厘米厚的地仗层(术语,壁画所附着的底层材料)上。地仗层的质地为灰色细砂泥,直接覆在殿堂土坯墙或佛窟的内壁,表面抹光压光,结实平整。壁画的绘制过程也大体可以观察出来:第一步先平涂大块底色;第二步以深蓝色粗线条勾画出形体的外轮廓;第三步细致填色,以平涂为主,辅以晕染,有些还表现出明暗关系和高光部位;最后用细色线或墨线勾定每个细部。多数壁画在完成后还在表面涂一层透明的桐油类的植物涂料。
壁画的颜料未取样做化学分析,但根据对壁画的观察和对藏族传统颜料的了解,古格壁画所采用的颜料大致有石青、石绿、土黄、土红、朱砂、白粉、金粉、靛蓝、连黄、木炭粉等矿植物颜料。按照传统,这些原始颜料在研磨成粉后都要加水加胶,调和使用。由于古格故城所在的阿里高原地区高寒缺氧,殿堂、佛窟多干燥、通风,壁画的自然破坏不大明显,至今还使大多数壁画保持着鲜艳的色彩和清晰的线条。
古格壁画的题材远较西藏其它地区丰富,就连各地常见的佛、菩萨、佛母、度母、空行母、天王、护法金刚、高僧大德等像也名目繁多,姿态各异。佛教中至高无上的崇拜偶像――佛,从古格壁画的藏文题名中可以找到60余种,如释迦牟尼、无量寿佛、无量光佛、普视佛、无忧佛、不败佛、金刚不动佛、无垢佛;能仁佛、世间自在佛、神圣涅架佛等等。
此外还有根据不同经典组合有序的三世佛、五部佛、七佛、十佛、三十五佛等。佛的服饰、形象分为两类:一类为正统的佛装,高肉髻,面相圆满,大耳垂肩,穿僧祗支(源自印度僧侣的一种长方形衣片,《大唐西域记》中记载这种衣服是“覆左肩掩两腋,左开右合,长裁过腰”),结跏趺坐,手结各式手印(具有各种含义的手姿)或捧执法器,如红殿北壁的佛像(图)。另一类为菩萨装,束高髻,戴宝冠,大耳饰环,上身袒裸,佩戴项圈、璎珞,肩披帛,下着长裙,结跏趺坐或其它坐式,如佛窟壁画中的无量寿佛。
菩萨的名目也很多,其中以各种文殊菩萨和观音菩萨占多数,明确题名的有圣智文殊、持密文殊、般若文殊、知识文殊、意文殊、语文殊、身文殊等20余种文殊菩萨。四臂观音、千手千眼观音、修心观音、普度观音、六字真言观音等10余种观音菩萨。菩萨虽多,服饰大体都一样,比菩萨装的佛装饰稍华丽一些,并且出现四臂、六臂、千手千眼等神异形象。
形象和服饰上最有独特风格的是多种佛母、度母,头束高髻,戴宝冠,耳饰大环,佩项圈、项链、璎珞。上身穿半袖紧身衣,袒露出双乳和小腹,腰肢纤细扭曲,手腕戴镯,下身穿长裙,结跏趺坐或其它坐式。
这种袒乳露腹的半袖紧身衣不见于西藏其它地区的同类造像,完全是受印度、尼泊尔直接影响的反映。佛母、度母依照佛经讲都是菩萨变化的女性,或者可以说是女菩萨,面相或慈祥、或娇媚、或端庄,也有少数作忿怒相。古格壁画中的佛母有顶髻尊胜佛母、白伞盖佛母、大宝佛母、作明佛母等20余种。度母也有白度母、绿度母、智度母、勇度母、善度母、解悲度母、解苦度母、解愚度母等40多种。
除了佛母、度母,壁画中还出现几十种女性神,如空行母、神母、天母、瑜珈母等。这类女性神祗形象各式各样,有的长着凶恶的兽头,有的乘骑骡马,有的舞蹈,有的飞腾,但共同的特征是全身赤裸,头戴宝冠或骷髅冠,佩耳环、项圈、钏、镯、璎珞等一应装饰。这里边最为凶神恶煞的就是吉祥天母了,她的形象与名号完全是两个极端。
肤色青蓝,红发上竖,头上戴着5个骷髅,右耳挂着狮子,左耳挂着小蛇,左手持骷髅棒,专门对付恶鬼阿修罗,右手端着盛满鲜血的骷髅碗,背上披着人皮。她的坐骑是一匹黄骡子,鞍前有红白两个骰子,红的主杀伐,白的主教化,骡子的缰绳是毒蛇,骡子的屁股上还长着一只眼睛。就是这尊凶恶丑陋的女神在西藏佛教中却有很高的地位,掌握着惩恶扬善的生杀之权。
古格壁画的偶像中护法神也是一个大的门类,可以找到各种明王。如马头明王、忿怒明王、大力明王、甘露明王;各种金刚,如大威德金刚、密集金刚、胜乐金刚、时轮金刚、橛金刚、智慧金刚;各种金刚手,如忿怒金刚手、勇武金刚手、花鹏金刚手、大虐寒林金刚手以及形形色色的护法空行、降阎魔尊、天王等。这些护法神多呈忿怒相或威严相,形象、服饰庞杂不一,姿态有坐、有蹲、有立。其中不少是多头多臂,胸前拥抱明妃的双身像。不明就里的人往往将这类双身像称为“欢喜佛”。
实际上按照西藏佛教密宗的说法,这些大都是受大日如来教令为降服各种阻碍修法的魔障而变化的明王、金刚。他们拥抱的明妃是修法的女伴,男女相合是悲智和合,调伏魔障,引向佛智的象征。明王、金刚和各种护法神都有各自不同的标识,注意观察大都能区别开来。
比如说马头明王的明显特征是在纷纭上竖的发顶伸出一个小小的马头,橛金刚则在手中握一金刚橛(金刚橛为法器之一,上部是金刚杵头,下部是三棱尖橛)。而密集金刚的标识就很复杂,红、黄、白三头,六手臂,两主臂持金刚杵,拥抱明妃,其余四手分别持法-轮、火焰掌、莲花和宝剑。明妃也是三头六臂,上两手勾搂密集金刚脖子,其余四手持莲花、弓、金刚剑等。明王、金刚、护法神在古格壁画中的服饰有几个共同点,上身赤裸,下身穿短裙或长裙,头戴宝冠或骷髅冠,手脚戴镯,胸前佩繁简不等的璎珞。
供养天女是古格壁画佛界人物中最为精采也最具特色的一类。对诸佛的供养依佛经有四供养、五供养、六供养以至于十供养。《法华经》的十供养包括:一供花、二供香、三供璎珞、四供抹香、五供涂香、六供烧香、七供缯盖幢幡、八供衣服、九供伎乐、十供合掌。供养天女就是天界专事供养佛的。古格壁画中的供养天女有供香天女、供花天女、供水天女、散花天女、熏香天女、掌灯天女、击鼓天女、吹笛天女、弹琴天女、善舞天女等20多种。
诸天女的形象装饰非常奇特,最典型的是坛城殿的天女像,头戴宝冠,长发后披,全身赤裸,四臂。耳饰大环,佩项圈、钏、镯,腰系璎珞,双乳正圆且偏高,腰肢纤细得超乎寻常,胯部往往做大幅度的扭动,有些明显露出阴部。四臂中有一对臂上举,手持法器,另一对臂在胸腹前作各种姿势,手持供器或乐器。这种全裸的四臂供养天女在西藏仅见于古格,姿态优美,线条流畅洗练,是古格画派的代表作之一。
佛陀的故事
白殿、红殿、度母殿的壁画中都分别出现佛传故事的内容,虽然在故事细节、表现手法和构图布局上有一些差别,但总体还是相同的。依照译成了汉文的佛教典籍,佛传主要为“八相成道”,具体包括下降兜率天、降母胎、出家、诣道场、降魔、成等正觉、转法-轮、示涅磐等。藏文佛教典籍则为“十二事业”或“十二宏化”,多出4项。具体为从兜率天下降、入胎、诞生、学书习定、婚配赛艺、离俗出家、行苦行、趋金刚座、降魔成佛、转法-轮、度化其母从天降临、示涅磐。
古格壁画中的佛传故事都是以藏文经典的“十二事业”为脚本,并将一些细节充分展开,以连环画的形式绘成分幅长卷或大幅组合,通过形象的画面讲述释迦牟尼的一生。可惜的是三座殿堂现存的佛传故事壁画都遭受不同程度的破坏,尤其是“十二事业”中的第一事业画面均已不存。
各殿壁画相互参照补充,基本上还可以勾画出后十一事业的故事情节轮廓。那么我们就从壁画现存的第二事业――入胎讲起。故事的情节原为诸天劝请菩萨下降南赡部洲,教示佛法,救度世人。菩萨问以何相下降,天神之子正感说:“据吠陀典籍应以白象形为宜。”
菩萨遂以六牙白象形入净饭王后摩耶夫人腹内。度母殿这一情节的壁画是这样表现的:画面左上侧绘一殿堂,菩萨居中结跏趺坐,手结转法-轮印,两侧有天人鼓乐供养。右下侧绘一房子,窗户极大,可见摩耶夫人拥被卧床,菩萨下方绘一白象,由一指示箭头从白象直指摩耶夫人腹部。
摩耶夫人怀胎十月,前往蓝毗尼园,手攀无忧树枝,菩萨从摩耶夫人右胁下出生,是为净饭王太子。其时大地震动,天降花雨,难陀、优波难陀二龙王为太子沐浴,各方呈现种种瑞相。太子降生后向四方各行7步,步步生出莲花。摩耶夫人生太子7天后寿终而往三十三天。太子由姨母摩河波阇波提抚养,并有怀抱保姆、哺乳保姆、拭污保姆、戏玩保姆各8个服侍。
有一黑仙人作出预言,太子居家将成转轮王,出家则成佛。古格故城三殿中都绘有表现这一情节的壁画:度母殿绘着摩耶夫人右手攀无忧树枝,上身赤裸,下着长裙,太子从右胁下出母体,下有两侍女托白帛准备捧接太子。白殿壁画表现了太子赤身立莲花上,两天龙持壶浴太子,四方各生7朵莲花,8位保姆怀抱太子等情景。红殿壁画的“太子受哺乳”图更有生趣,赤条条的小太子跪坐在哺乳保姆怀中,双手捧乳头吸吮,袒乳露腹的保姆似乎还有些羞涩,面孔微微左转。
太子年纪渐长,净饭王命太子向4位老师分别学习文字、算法、射箭、驭象,但太子天生就已具备知识和技能,诸位老师反倒要向他请教。度母殿壁画中我们可以看到太子盘腿坐于坐垫上,与老师相对低首观书,但其它情节的壁画已被破坏。太子成年,释迦族长老乞请净饭王为太子选配成婚以防其出家。太子遍选婆罗门、王侯及庶民女子,只相中释迦种姓持杖者之女俱夷。
持杖者提出让太子与其他释迦族青年比赛技艺以察其能,净饭王应允。俱夷竖得胜旗,约定比赛驯象、射箭、角力等项,胜者夺旗。释迦族青年拉金首先上场,一掌击倒一象,阿难陀又上场将象抛出城外,太子则以脚挑象抛出一俱卢舍(印度古距离单位,合5里)远,落地成洼。
难陀、阿难陀接着与太子角力,一交手便扑倒在地,拉金继上,太子将其抡上空中又轻放置于地。最后赛射,在2由旬(一由旬为40里)外悬铁鼓一面,其他3人只能射6俱卢舍远,而太子在10俱卢舍远悬置7面铁鼓,其后又悬铁猪,一射而穿七鼓一猪,箭入地成穴,名之箭井。度母殿壁画中较详细地表现了这些情节,如拉金击象,太子以足挑象,太子抡起拉金,持盾格斗,太子力射7鼓及铁猪等。白殿壁画也保留有同样内容。
太子成婚后,诸天恐其耽于世俗声色,纷纷从天界向太子发出偈语,提醒他不要被痴暗所缚,速离欲境发起菩提心。太子出游四门,见老、病、死及修行比丘,又观农夫驱牛耕田,深感人间疾苦,决意弃绝尘世,出家修行。晚上太子又看到白天欢歌的宫女在睡眠时都呈现出丑陋的姿态,更觉尘世无可留恋。
当夜令御夫备好宝马,由帝释天引导,四天人托住马足腾空窬城而出。行至清静塔前,太子将宝马及自己身上服饰交御夫一并带回,太子就地以剑削发,诸天神请发造塔供养,净居天随即奉上袈裟。净饭王得知太子已出家,派500侍从前往相伴,太子只留5人,其余遣返。佛传“十二事业”中以此事业情节最为繁多,壁画中往往以数个画面来表现。白殿壁画中就分为观耕、观众宫女睡相、御夫备马、窬城而出、以剑削发、遣返御夫及宝马、收五侍从等情节。
太子出家后带领追随他的五弟子来到尼连河畔,决意修禁行和苦行,住修6年。每日只食一粒芝麻、一粒柏实、一粒米,体瘦如枯木,甚至腹显后脊。附近农人不解,寻机扰害,均末得逞。红殿壁画中绘有出家成为菩萨的太子坐在树下修行,五弟子围坐其周,均结跏趺坐,手结禅定印,身体枯瘦,筋骨显露,但神态安详,稳坐如磐石。同一幅画面还表现两个农夫各执一棍捅菩萨双耳,菩萨不为所动的细节。
菩萨虽经6年苦修,但仍不得解脱,遂欲受食以增强体力,进而准备修习四禅定。此时有善生母二人煮炼千头黄牛之乳,又有二仙人加入生威光之药,菩萨受而食之,体发金色,遂让乳钵随水漂走,龙王得之。菩萨又剃下胡须使善生母获得并供养。五弟子见菩萨受食,疑其修心不坚便离之而去。红殿壁画在两个画面中集中表现了善生母挤乳、炼乳、仙人赐药、善生母捧体供乳糜、龙王获体、剃须赐善生母等细节。白殿壁画在同样内容后还绘五弟子告辞等情景。
菩萨沐浴受食后体力充沛,运大士气力来菩提树下,安住正念坐金刚座上,发誓不证得无漏绝不散此跏趺。魔王召众魔显极恶相,向菩萨射掷各种兵器,并让妖艳魔女展现32种媚术。菩萨生起三明四禅定,使射来矢石化为花朵,使妖女变成老妪,以手指地召地坚母现出半身合掌作证。黎明时分,菩萨通达十二缘起及四谛,现证了正等正觉而成佛。
红殿、白殿壁画中都用数个画面大肆渲染了释迦牟尼这段最为辉煌的历程,如降魔、得道成佛、毗沙门天王供钵等。其中降魔的场景最为精采,佛陀结跏趺坐于金刚座上的吉祥草和覆莲上,右手指地召地坚母作证。背后是枝叶茂盛的菩提树,两侧是魔王召集变化的各色妖魔,或拔剑张弓、操枪舞棒,或举石擎火,欲抛欲掷,或变化狮虎熊豹,狂吼怒嚎,三魔女则袒乳露阴,搔首弄姿引诱佛陀。佛陀稳坐树下,安详自在,各种飞来的兵器化为花朵,魔女变为丑陋的老妪,地坚母自地而出,合掌作证,种种细节历历在目。
菩萨成佛之后诸苦皆无,具足善乐,先往林中修习49天。此时大梵天请佛陀为利益众生而转动法-轮,为众说法。佛陀来到鹿野苑,受供食后绕三佛座三匝而坐于第四座上,放大光明,天神在佛前供千辐金轮。佛于后半夜开示五比丘,宣传正法,陈如当即证得阿罗汉果,至此“三宝”(佛、法、僧)具足。佛陀先后转法-轮三次,初转四谛法-轮,二转无相法-轮,三转胜义抉择法-轮。
接着佛陀又在王舍城分别接受舍利弗、目犍连二人以及优为、那提、伽耶三人的皈依。红殿壁画中有一幅佛转法-轮图,佛陀结跏趺坐于莲座上,手结转轮印,座上饰法-轮及双鹿,喻示鹿野苑初转法-轮。背后饰帷帐,顶覆华盖,各路天神、五比丘及外道瑜伽行者跪坐两侧倾听说法。还有一幅是表现舍利弗等人皈依佛陀的情景:一条河边山峦起伏,野鹿出没,佛站立在菩提树下,左手托林,右手结印。舍利弗等5人在佛前合掌而立或跪拜,众比丘在旁成行列坐,注视着眼前的5位皈依者。
菩萨成佛7年后,为度其母而往三十三天(忉利天)为母说法,然后经吠琉璃宝桥(一说天梯)返回。这个情节在西藏清代卷轴画中通常表现为,一架直达云端的长梯上佛陀缓步而下,上为天界,下为尘世,梯下有众比丘恭候佛陀。不知为何在古格几个殿的壁画中都没有这一情节的内容。
佛陀本可住世到劫尽之时,但为了显示诸法无常,佛曾答应入涅磐。佛赴扎金城途经波旬城时病倒,弟子阿难取迦拘达罗河水浴佛足,佛稍康复,安抵扎金城。在娑罗双树间置床座,佛右胁贴卧,双足重叠,作明空想念,俱正念正知。佛为了度化圆满,又现为乾闼婆调伏极贤、极喜二人,然后展示身容,入四禅定而涅磐。时大地震动,天乐齐鸣,流星陨落,众比丘悲痛欲绝。
佛涅磐7天后,迦尸那城所有力士设置好奉安佛身的床座,诸天神供名香、幡盖、璎珞,将佛身置宝天冠塔前,天神散花及膝深。等大迦叶来到,佛身下香木不点自燃。荼毗(火化)后的佛舍利共有12摩揭陀大升,有8国王族前来争夺舍利。婆罗门平斛氏力劝众王,主张将舍利分作8份,众王同意并将分得的舍利迎回建塔供养。平斛氏分得舍利瓶,当地的毕体人分得火化佛身的炭灰亦建塔供养。
共计建有八舍利塔、一瓶塔、一炭灰塔。白殿壁画中有三个画面表现示涅磐事业:第一幅绘佛陀横卧双婆罗树下的床座上,佛之上装饰花朵组成的华盖和璎珞,弟子阿难抚佛足悲泣。上下有11弟子身处火焰中,最上方绘两尊侧卧床上身燃火焰的佛陀;第二幅正中绘佛陀身置宝天冠塔上,烈焰升腾,下有19位比丘,上有诸天,齐向佛陀礼拜;第三幅正中一塔座,座上为堆成馒头状的舍利,两天人正在揭开覆盖其上的帷幕,右下角一舍利塔,塔前有8王等侯分舍利,上有诸天供养。除西藏佛教典籍中“十二事业”的各种情节外,壁画中还有一些画面在查阅其它经典后也考证了出来。
如红殿的佛传壁画中有这样一个画面:佛陀结跏趺坐于莲座上,双手结禅定印,一蛇(龙王)盘绕在佛的上身及头后,上护其顶,天空有一团云正在降雨,周围有三天人跪礼。根据律藏《大品》,佛陀成道后分别在三处定坐,安享解脱之乐。当时遇到天降大雨,龙王目支邻陀从其住所出,绕佛身七匝,并以其头遮护佛陀,情节恰与此画面吻合。
红殿还有一幅画面,绘佛陀左手托体,右手持锡杖,率众比丘外出化缘乞食,一白象以鼻卷剑进攻佛,佛右手发出火焰,象被制伏,掉头遁去。
根据《小品》,佛陀晚年时,弟子提婆达多欲与佛陀争夺僧团领导权,在阿阇世协助下图谋杀害佛。他先雇佣刺客,但刺客一走到佛面前即被感化。后又从灵鹫峰推下大石砸佛,山挺身阻止了石头。最后又在佛率僧化缘乞食的路上放出一头疯象,但还是被佛制伏了。这幅画正是描绘了这一事件的部分情节。
地狱变图也是佛寺壁画常见的内容,古格故城的坛城殿和山顶王宫区的护法神洞窟壁画中有内容和表现手法大致相同的两幅长卷。其中坛城殿壁画的场面较大,以长卷形式环绕殿堂一周。图中所绘各色罪人或身首异处、肢体分离、尸骨横飞,或倒挂树上、漂流水中。
恶魔追赶打杀罪人,虎豹豺狼鹰鹫撕扯吞食罪人,尖利的木桩从罪人尻部洞穿至顶,烈焰熊熊烧烤着罪人,种种景象惨烈之极。其中还夹杂绘有尸林修行的瑜伽行者,水中观望的龙王以及山石树木、江河湖泽和各色佛塔。地狱为佛教“六道”(天、人、阿修罗三善道,饿鬼、畜牲,地狱三恶道)中的三恶道之一,佛经中有“八大地狱”、“八寒地狱”、“十八地狱”、“一百三十六地狱”之说。从坛城殿的地狱变图内容分析,应属“八大地狱”中以各种禽兽、各类刑具惩罚罪人的“众合地狱”。
古格的“清明上河图”
古格壁画中最珍贵也最有研究价值的是一批直接反映古格王室、贵族、僧侣、平民宗教生活和世俗生活的壁画,可以说这些壁画是古格的“清明上河图”。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当时古格王室、贵族、僧侣朝礼佛陀,高僧说法讲经,喇嘛辩论,庆典乐舞,杂技表演,商旅运输,外邦贡物等一系列生动的场面。
表现王室成员参与的礼佛图仅有一幅,绘于红殿东壁的下部,场面宏大,人物众多。居中是一尊端坐莲台座的无量寿佛,僧俗两界人物分列左右两侧。僧人在佛的右侧,分8组成行列坐,共计有73个人物。其中有5位僧人与众不同,形体较大,坐垫华丽,居于上首。其余的一般僧侣则拥挤地列坐在右后方和下方。看起来在僧侣集团中等级还是很明显的。
国王、王子、王室家眷、大臣、贵族列坐在佛像的左侧,国王和王子当然居于最显赫的位置。父子俩的服饰大体相同,头缠红色花巾,衣穿红地黄花长袍,外罩及膝半袖长衫,脚穿白色长筒靴,盘腿坐在三层锦缎座上,后有靠背,身后各有一童子高擎华盖遮护在他们的头顶。国王、王子左后侧的4位小王子的服饰、坐垫就大为逊色,头不缠巾,服装简单,坐垫也只有一层,其中只有一位王子有侍童在侧服侍。
王后、四王妃、四公主排列在国王和众王子之下(图)。王后像较大,长发辫后披,头顶有金色顶饰,上身着蓝地长袖衫,下穿黑红竖条长裙,外披红地黄花披风,跪坐于双层坐垫上。左手持一柱线香,胸前露出10余条珠串连成宽排的项链。4位王妃与王后的穿戴基本一样,但坐垫只有一层,靠背也略小。王后和每位王妃身旁都跪坐一侍女或侍童。4位公主列坐在王妃左后,除了长袖衫统一为黑色外其它服饰同王后、王妃。
大臣和贵族有14人,分上下两排坐于王室成员左侧,发式和服饰与4小王子没有大的区别,但服装颜色较为驳杂,五颜六色。再向左是民众和外邦来宾的礼佛行列,民众分4排跪坐48人,均合掌胸前,面向右侧。外邦来宾的装束打扮明显不同于古格人,多蓄胡须,头缠白巾或黄巾,结跏趺坐或跪坐在为他们设立的专席上。
王室成员和大臣、贵族礼佛者的下方陈列着外邦礼佛者所贡献的各类礼物,可看出有布匹、酥油包、牛羊肉、红糖包、罐、瓶、法器、珠串、珊瑚、杂宝等物,有两位侍者正在搬运酥油包。礼物的左侧还可看到正在赶来的送礼者,或驱逐驮着行囊的牛马,或背着装满礼物的背篓。
高僧说法图见于坛城殿的东壁,图中一高僧头戴尖顶僧帽,内着僧袍,外披袈裟,结跏趺坐于坐垫上,手结说法印。南侧一弟子手提香薰侍立,另有12位弟子分三行结跏趺坐,合掌倾听高僧说法。
喇嘛辩经图只见到一幅,绘在白殿壁上。图中僧俗佛教徒排列5行,俗装的佛教徒们肩披长发,身着长袍,足蹬高筒靴,结跏趺坐或游戏坐观看僧人辩经。僧人着无袖僧袍,被袈裟、多戴尖顶僧帽,下两行列中各有二僧人相对站立,击掌发问或应答,其他僧人坐于垫上观听。
热闹的庆典乐舞场面分别绘于白殿和红殿,以红殿保存得最为完好清晰。画面中10个古格盛装女子横列一排,交臂牵手,踏地起舞,舞姿和缓沉稳。12个鼓手二三成行散立,以槌或手击鼓为节,一扮成天女模样的女子在旁敲锣。10个号手分5对分别吹奏5种长短不同的号,一男一女表演跑驴。一只由数人装扮起来的大狮子昂首徐进,狮前有扮成猴形的人在耍逗,后有扮成恶鬼的人在追赶,还有僧俗6人前呼后拥,气氛热烈,秩序井然。
白殿的庆典乐舞图侧下方还绘有几组杂技和体育表演的精采场面:一组为爬杆、滑杆,中间直立一主杆,两侧各斜撑一杆,顶端绑扎在一起,一人刚攀爬至顶,另一人骑跨斜杆下滑,并将双手上扬保持平衡;下方一组3人,一人倒立以手行走,一人伏卧在一竖立的短棍上以棍顶腹旋转,一人表演侧手翻,旁边有2女子敲锣助兴;中部是马技,一人倒骑马背,回首策马急驰,另有4人骑马回首,张弓欲射。
商旅运输图散见于白殿、红殿和大威德殿。红殿的运输图与庆典场面合为一体,图中7个古格男子各负一根木料,3只牛各驮两根木料,7只驮羊各驮两只木箱(西藏西部游牧人把羊也作为运输工具,在羊背左右搭驮小背袋或小木箱成群驱赶,长途运输,前些年还可见到长途驮运湖盐的羊群),队尾两个印度商人(?)似在押运。两人均短发络须,上身披巾,腿脚赤裸,前者拄棍而行,后者以棍挑两个水葫芦。白殿运输图描绘的是一支运木料的庞大队伍,有30多人背负或抬运木料,内有数名僧人也负木随行,队前有一官吏骑马带队,队中还有3只耗牛也驮着木料。
如果仔细观察每一幅壁画,就会发现有大量的动物、植物、山水、建筑点缀或陪衬其间。动物形象一般比较写实,尤其是当地常见的牛、马、羊、狗、豹、鹿、羚、鹰、鸟等都描绘得生动逼真。而佛教中的神圣动物如象、狮、孔雀、摩羯鱼、龙等则多夸张变形或拟人化,有时还将两种动物相组合成怪异造型。如摩羯鱼鱼头龙身、鸟头狮身、前半身是马后半身是龙等。特别应当注意的是一些动物身体后部附加或直接变化出忍冬纹样的做法,明显是受到印度阿旃陀石窟壁画图案的影响。
植物图案有树木和花草两大类。树木除少数较写实外,大多夸张变形。树冠有花朵状、桃状、伞状、蘑菇状、笔头状等程式化形态;树叶大致有卵形、桃形、橄榄形、花瓣形等;树干粗细曲直不等,大多饰繁简不一的忍冬纹。整个树形具有浓郁的装饰意味,很多已完全图案化。花草多用来装饰造像的座,以莲花和忍冬卷草最为常见。
山峦、河湖、云朵等均不写实。山峦大体有两种形式,一种为馒头状,一种为钝角峰状,线条内侧通常稍加晕染。河湖的外轮廓也就是河岸、湖岸加莲瓣边,水波画成繁复密集的鱼鳞状。云朵有两种形式,一种为忍冬旋涡状,一种为如意团状。
作为点缀的建筑图,多为装饰性的藏式楼阁立面图,散点透视,缺乏立体感。一些屋顶加有带刹的攒尖顶,屋内外坐立人物。
古格壁画不论从内容、题材还是从构图、色彩、线条看,都具有自己的独特风格,很难简单归入西藏传统上熟知的“藏孜”、“康孜”、“卫孜”三大画派以及邻近的尼泊尔画派。但古格王国地处数种文化的交接地带,艺术风格不可避免地受到多方面的影响,由于我们对境外的艺术流派缺乏深入的了解,一时还难以作出细致具体的比较。从总体风格来观察,古格壁画与流行于后藏的“藏孜”画派有接近之处,也可以看出一些尼泊尔画派的影响。
“藏孜”画派的特点是设色沉着饱和甚至有些浓艳,线条简约而流畅,单线平涂结合晕染,人物形体饱满,追求曲线变化。尼泊尔画派着重用色,多用色线勾勒,层层晕染,布局上常见以大像为主体,四周或两侧排列相关的众小像,格式严谨,讲究左右对称。古格壁画既将这两种画风兼容并蓄,又坚持体现古格自己写实、质朴的传统特征,尤其在礼佛、辩经、庆典乐舞、杂技、运输等场面以及动植物的描绘上表现得更为突出。
此外,在古格壁画中还可以看出印度晚期佛教艺术(公元7-9世纪)和10世纪以后印度教艺术的影响痕迹。在观察坛城殿壁画中的供养天女时,这种印象会更加清晰。特别是大像背光中的摩羯鱼、马、羚羊、孔雀等瑞禽瑞兽的前半身保持原形,后半身演变成繁缛的忍冬卷草纹,与印度阿旃陀石窟壁画中的同类作品如出一辙。汉族地区佛教壁画的影响在古格壁画中难以寻觅,但在年代最晚的度母殿壁画的侍立菩萨身上显露出间接影响的迹象,这很可能是随着格鲁派(黄教)势力在阿里地区逐步扩展而带入的“藏孜”画派新风格的表现。
古格壁画年代的推定是和对建筑年代的推定交织在一起的,但两者不一定完全保持一致。西藏佛寺没有在壁画上题书年款的习惯,古格也是一样,所能用于分析的只有壁画中出现的年代不同的高僧、译师的题名。这类题名画像多达500余尊,但重复出现在各殿的情况较多。可考其年代的有相当于古格早期(12世纪末以前)的数十位高僧,相当于古格晚期(15世纪以后)的数位格鲁派高僧,而独缺相当于古格中期一段时间的西藏各教派著名高僧的题名画像。
引起我们注意的是5座现存佛殿壁画中都出现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的题名像,只不过表现形式和题名方式有所不同。红、白两殿和坛城殿中的宗喀巴像均为小像,题名时直呼本名“杰罗桑扎巴”。而大威德殿和度母殿都绘成大像与佛像并列,题名也成了较晚的尊称“宗喀巴”,两侧还绘两位弟子。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红殿、白殿、坛城殿壁画的年代大约在15世纪中叶到后半叶,大威德殿、度母殿壁画大约是l6世纪初至中叶的作品,其中度母殿的最晚。
从壁画风格来看,早晚之间有明显的变化。较早的红、白殿壁画题材丰富,同题材图案也变化较多,仅是各种造像的背光就多达10余种,加上背光细部的一些变化至少有30种以上。人物形体饱满而不雍肿,生动而不媚俗,色彩华丽而不妖艳,线条纤细而不显柔弱,布局富于变化而不显杂乱,绘制过程中有一定的即兴发挥成分。
到了大威德殿,壁画布局开始变得单调,过分讲究对称,略显呆板,但用线设色还比较讲究。到最晚的度母殿壁画,早期丰富多采的造像背光只剩下两种形式,人物造型严重程式化,线条虽还流畅但变得更柔,设色开始出现金粉、沥粉。佛传故事画的背景色变为绿色,更加接近卫藏地区明清时期的壁画风格。
五彩缤纷的天花板
西藏其它地区寺院殿堂中不大着意装饰的天花板,在古格人眼中却是一片表现装饰彩绘技巧的绝好版面。古格故城现存的5座佛殿中只有度母殿一座没有天花彩绘,其余4座的天花板全都绘满了彩色图案,使整个殿堂满目生辉。经我们统计,4座殿堂的天花彩绘图案多达626幅,总面积有780平方米左右。
这些彩绘图案在单元图案的选择和整体构图上均不雷同,但风格特点基本一致。画面充实拥挤,每幅画面由数种至10数种图案单元组合搭配构成。设色浓艳,平涂施色,较少晕染,多用色线勾勒,很少用墨线。
构成整体画面的基础单元图案的题材丰富庞杂,分类统计至少有130种。大致可以归纳为人物、动物、植物、法器及吉祥物、美术体梵文、云纹、几何纹等。
人物类中数量最多的是绘在莲花式曼荼罗图形中的佛、菩萨小像。由于形体过小,细部的表现较困难,一般只求大轮廓,难免有千佛一面的现象。白殿和大威德殿每幅天花板的中央几乎都是这样的莲花式曼荼罗及小佛、小菩萨。数量较少的度母像、天王像与壁画中的同类造型相比似乎也并无特色。与壁画造型、技法迥异的是形形色色的伎乐天、飞天、力士等天界的小人物。
伎乐天均为舞蹈天女,服饰大同小异,长发挽髻后拖,或戴花冠。上身穿紧身半袖衫,袒露胸乳和小腹,肩披飘帛绕前臂外飘,下穿长裙作舞蹈状,腰肢扭动,手姿各异,动感极强。有的伎乐天还作跳跃状,双手持花穗起舞。飞天有男女性之分,其中白殿天花板中一幅四飞天图较奇特。四人中男女各半,围绕四出云朵牵帛起舞,对角布置在一个方框内。力士的造型和构图更为多样,有单人、双人、四人之分,形象大多是后拖髻,身饰大环,上身裸、下穿短裤,作奋力托举或舞蹈状。
较典型的有四力士托举法-轮图,四个力士以不同姿势环绕法-轮,或以双臂拥托,或以胸背顶托,动作幅度较大,略加夸张。另有一种四联力士更是妙不可言,正视若两背相靠,侧视若两腹紧贴,腹背间以帛束成十字形,只绘两个人体,却可看出四个人体,有一种魔幻效果。动物也是图案中常用的素材,计有龙、凤、狮、象、摩羯鱼、鹿、羚羊:独角兽、马、孔雀、迦陵频迦鸟、鸭、雁、鸥鹅等10余种。
每种动物又有各种形态,如龙就有单盘龙、单走龙、双龙缠绕、四龙缠绕等。我们选择一些较为典型的小作欣赏。红殿天花板中有一幅双缠龙图,两龙相对跨骑,后足站立,前半身从对面胯下钻出向上弯曲回首,两龙头相对,口吐火焰,周饰数朵彩云。白殿的单凤展翅是一个适合纹样,凤硕体长颈,正面展翅,翎羽长若飘带向
两侧飘舞,头周延伸出火焰状纹,整个形体巧妙安置在一个柿蒂形框中。交颈双凤图是在一个长方形框内进行构图,两凤长颈相交绕,展翅双飞,尾铳翎下部及两侧飘曳飞动,风口各衔一枝忍冬莲花,使画面更为充实,采用对角构图,平衡对称。以交颈的形式表现对兽的还有一种双独角兽图。兽体略似雄狮,头部丑陋怪异,顶生独角,两兽抬足相向,绕颈回首,尾部上翘,似在亲昵厮摩。动物图案中也有像四联力士那样的构图,两狮背对背相靠,腹背间束十字交叉宽帛带,转90。
看又似腹对腹相贴的双狮。摩羯鱼原为印度神话中一种长鼻利齿,身尾似鱼的神兽,传为水天、夜叉之乘骑,又是恒伽女神之化身,古格天花板图案中多见。其形象上吻长而上翘,短角小耳、头似龙,身尾如鱼,遍体覆鳞。白殿有一幅圆形图案的单摩羯鱼较为典型,整个身体盘踞于圆内,长舌伸出变为忍冬卷纹,鱼尾上卷成扭曲螺旋的繁缛忍冬纹。
红殿的一幅双鸭背立图是禽类图案中的杰作,图中两鸭相背挺立,口衔折枝忍冬莲花,贴胸饰上卷的忍冬纹,立于覆莲座上,座两侧各伸出一支折枝忍冬,采用严格的轴对称构图。此外,四雁环立图、四兔追逐图、鸥鹅牡丹图等图案也很精采。
植物图案大多为变形的花草,很少有写实的。因为已经是失去原形的装饰性图案,很难一一分类辨识,大致可看出多是莲科、菊科花朵和忍冬卷草类图案。花朵既有盛开状的,也有半开和含苞待放的,衬以花叶组合不同图案。忍冬卷草几乎全部以二方连续的方式构成条状图案,还有一些变形忍冬作成圆形、菱形、梭合形的单元图案。
在人物、动物、植物三大类图案以外,还出现金刚杵、金刚剑、摩尼宝珠、八吉祥物、杂宝(通常包括莲花、祥云、金铤、银铤、方胜、犀角、珊瑚、宝珠等,集中对称排列)等法器以及宝物图案,六字真言、十相自在等美术体梵文图案,流云、万字云、四出如意云等云纹图案以及龟背纹、毬路纹、琐纹、方胜纹、方套纹、八角纹等几何图案。
在天花板彩绘图案的构成与组合方面,古格的画匠们几乎使用了所有图案构成的方式,如对称、平衡、适合、二方连续、四方连续、散点、重叠等。通过精细工巧的安排,具有充分想象力的设计,制作出一幅幅完整紧凑、变化多端、绚丽多彩的图案。
刻在卵石上的艺术
古格故城保存至今的石雕作品除一件高浮雕的石佛造像外,主要是4000多件线刻造像石和藏、梵文经咒石,这种石雕在藏语中通称为“玛尼石”。玛尼石大部分嵌在故城遗址北部缓坡地带的几道夯土或土坯砌筑的墙体上,个别窑洞门外的崖壁上也偶有镶嵌。嵌于墙体的玛尼石因墙体剥落坍塌,绝大多数坠落墙下,但保存尚好。玛尼石除少量为石片以外,多为稍扁的天然卵石刻就。
卵石的磨圆度较好,表面较光滑,大小在20一60厘米之间。雕刻的技法基本是减地阴线刻,刻纹较浅,但清晰可见。雕刻的题材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各种造像和佛塔,造像包括壁画中常见的佛、菩萨、金刚、天王、度母、佛母、高僧、法王、供养人等;另一类为藏文或梵文的六字真言、三字真言及其它经咒短句。
受材料质地和面积的限制,玛尼石的造像不可能在一块石面上雕出较多的人物,细部的表现也不可能刻画入微。造像多为单体,只有少数几块刻三人组合的一铺造像,背光、头光仅用一种简单的带状环表现,不加纹饰。对卵石形状的选择往往根据所刻造像的需要,站立的像选择稍长的椭圆形卵石,坐像选择稍圆的卵石,三人组合像则将长椭圆卵石横置布局,充分利用卵石的自然形状因材施雕。
造像的种类比较丰富,佛像有近10种,有立姿,有坐姿,有释迦牟尼,还有药师佛、无量寿佛。其中一件释迦牟尼成道像刻在略呈长方形的卵石上,释迦牟尼外披袒右袈裟,内着齐胸长裙,结跏趺坐于覆莲座上,右手结指地印,左手结禅定印,头光上刻菩提树的树冠,象征释迦牟尼在树下修行证果,得道成佛。菩萨和度母像有30多种,一眼就可以看出这些造像与古格佛殿壁画中的造橡保持着完全一致的风格。
如度母像一样是高髻宝冠、耳饰大环、上身穿半袖紧身衣,袒裸双乳和小腹,乳圆腰细。以四臂观音为中心的知法三尊像是少数几件多人组合像刻石之一。四臂观音居中结跏趺坐,右侧刻怒发冲冠、跨步而立的金刚手,左侧是一手持莲花、一手挥剑的文殊菩萨。三尊像共有一个三弧连体背光,这种背光在壁画中是见不到的,只有在因材施雕的玛尼石上才会出现这样删繁就简的形式。在壁画中多头多臂,佩饰复杂的大威德金刚、六臂玛哈嘎拉(大黑天)等护法神像在被刻在玛尼石上时也都作了简化处理,突出特征,抓住动态,线条简约,轮廓清晰,整体效果很好。
几十位高僧大德也成为玛尼石表现的重要题材,一些在壁画中不太引人注目的高僧像单独刻在石上便一下子醒目起来。有一块玛尼石上刻着米拉日巴尊者在洞中苦修的图像,这是一位西藏佛教史上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一生实修苦修,坚韧不拔,成为噶举派的第二代祖师。
图中的米拉日巴肩披长发,穿袒右长袍,结跏趺坐于坐垫上,左手托腮,面露微笑,右手搭膝,坐姿随便,丝毫没有一殷苦修者严肃拘谨的味道,生动刻画了米拉日巴的本来面目。他身周及两侧的曲线象征山洞,身右侧刻一灶,灶上反扣一双耳釜,巧妙地反映出苦修中的生活气息。
三法王像是玛尼石中的一件重要作品。所谓“三法王”是指吐蕃王朝弘扬佛法的松赞干布、赤松德赞、赤热巴巾三王。造像刻在一块椭圆形的大卵石上,三位法王的服饰与壁画中古格王室成员的一样,头缠巾,耳饰大环,长袍加身,足穿长筒靴。
中间是松赞干布,头顶显现出佛头,左手结大梵天王印,右手结与愿印,左肩托一朵莲花;右侧应为赤松德赞,双手结转轮印,两侧各一莲花,花上分别托金刚剑、经书;左侧是赤热巴巾,两侧莲花上托金刚杵、金刚铃。三像共坐一个大覆莲座,背后是连为一体的三连弧背光。
贵族妇女诵经礼佛图同样是一件极有价值的刻石。卵石上部刻垂帐,左上角有一尊小佛像,正中的贵妇头梳长辫后披,内着长袍,外披披风,盘腿坐在坐垫上,服饰与壁画中的王家女眷相同。贵妇一手持念珠,一手摸经书,经书下是交叉腿的活动经书架,右侧刻一个花边小柜,柜上置一水壶和一个插着花的小瓶。
藏文六字真言刻石都使用藏文的“乌间体”(喇嘛多用此体抄经,刻版印刷也用此体,故俗称“喇嘛体”,相当于汉字的楷书)字母,有不少还在石上加饰莲瓣纹、双鱼纹、伞盖纹等,使千篇一律的六字真言刻石有一定的变化。梵文的六字真言刻石多使用兰查体,只有一件使用悉昙体,这是西藏13世纪以后不大使用的字体,很可能这件刻石的年代较早。
古格故城的玛尼石数量很大,绝非短时间所能刻就,但从风格和题材上又看不出阶段性的变化,孰早孰晚无由推定。与西藏的卫藏地区相比,古格的玛尼石刻具有一定的地方特点:1.选材大多为天然卵石,不加工整形,择较大的光洁面凿刻造像或文字(卫藏地区以石片为多);2,刻工较工细,线条圆润流畅,轮廓清晰(卫藏地区较粗犷);3.以造像为主,题材较宽泛,包括了古格壁画中大多数造像类别(卫藏地区以藏文六字真言为主,造像的类别较少);4.大多数玛尼石镶嵌在夯土或土坯砌筑的墙上,形成壮观的“玛尼墙”(卫藏地区多堆置山顶、山口、道旁、寺旁)。
方寸之间的众神
古格王国故城遗址还发现一大批袖珍佛教艺术品――模制泥造像(包括小泥塔和经咒印泥)。这类造像在藏语中称为“擦擦”,是用雕刻的金属模按入软泥,磕印而成浮雕效果的泥饼。大者盈尺,小者不足方寸,刻画入微,毫发必爽。题材有佛、菩萨、度母、天王、金刚、高僧、佛塔、经咒等。泥像制成晾干后通常要经过喇嘛诵经施法,方可作为正式崇拜物置入塔内或供入寺庙。有些还直接堆放在山洞或山上的巨石下供奉,也有放入小佛盒随身携带作为护身符者。
古格故城采集的模制泥造像均出自残塔座、殿堂和一些窑洞内,以窑洞和塔身内采集的数量为多,仅ⅷ区2号窑洞内堆置的小泥像就达万枚以上。数量虽巨,但种类只不过30多种。经过整理我们分为9类,不外乎是壁画、玛尼石刻造像常见的佛、菩萨等,只是材料不同,表现形式不同而已。
佛像类有6种,比较典型的是一佛二弟子像和无量寿佛六尊像。一佛二弟子泥像高7.4厘米,比一个香烟盒略小,外形呈圆拱形。佛陀结跏趺坐于双狮须弥座的覆莲座上,佛两侧侍立比丘相的二弟子,须弥座以上的外周饰草叶纹、火焰纹双重背光,背光内有不太清晰的藏文经咒,背面捺印八塔纹。无量寿佛六尊像整体外形略呈长方形,六尊造型相同的小佛分为上下两行,每尊像大小如花生米,眉目不清,服饰还都看得出来,后背有制作时留下的手掌纹。
菩萨类有3种,以一枚菩萨立像最为漂亮。菩萨头戴宝冠,面带微笑,上身裸,宽肩细腰,腰肢稍扭曲,下穿贴腿长裙,有“曹衣出水”之感。披帛、花带由颈后绕臂前飘下,花带环绕腿前。
天王类、佛母类各仅一种,度母类有4种。与众不同的是二种较薄的浅浮雕度母像,泥片外形呈圆形,度母束高髻,佩项链,上身棵,下着长裙,结跏趺坐于仰覆莲座上。双手各持一茎莲花,有桃形头光而无背光,像的周围遍布藏文经咒,整个直径仅4.8厘米。
护法金刚类最丰富,有10余种,如大威德金刚、智慧勇识金刚、密集不动金刚、胜乐金刚等。其中大威德金刚像外径3厘米,只比五分硬币略大却精细地表现出牛头人身的大威德金刚的几乎所有细部,令人叹为观止。
双身胜乐金刚像更为复杂,金刚有4面,每面3睛,12臂。两主管手持金刚铃、杵,拥抱明纪,其余10臂分张两侧,分别执各种法器。身体几乎全裸,腰系虎皮,50人头链由颈后绕臂前垂于裆下,足下踏两人。明妃全裸,左臂勾抱金刚脖颈,右手上扬金刚杵,腰臀佩璎珞,双脚勾于金刚腰后,像周饰火焰背光。
塔印类有5个品种,全部采集自故城东3公里的卡尔普遗址的残塔座中,是用一种类似封泥印章的印模在薄泥片上压印制成,有梵文单塔、藏文单塔、3塔、10塔、17塔等。17塔的塔印较清楚,中央为一大塔,两侧各一塔稍小,上两侧各一塔又略小,其余的12塔小如绿豆,轮廓已不清。中间5塔均表现出座、身、刹三部分,塔座形制各不同,可辨中央为天降塔,左侧为吉祥多门塔,右侧是菩提塔,空档处遍布藏文。
模制泥造像的做法源出印度,属于佛教中造像功德的一种,制作并供养可荐福禳灾。义净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载:“归东印度,到三摩坦吒国,国王名曷罗社跋乇……每日造拓(脱)模泥像十万躯。”并说“西方法俗,莫不以此为业。”可见当时印度此风之盛。
佛教东传汉地,北传西藏,其俗也随之而入。汉地尤以唐代为盛,寺僧、百姓纷纷以此为善业,制像供养。当时称这种模制泥像为“善业泥”、“善业佛”、“脱佛”,将同时制作的小泥塔称为“脱塔”。敦煌晚唐卷子中有数篇《印沙佛文》中记载制作模制泥佛像的盛况。
西安作为唐代的首都也多次出土此类泥佛像,形制、题材有10数种。从泥佛后背题记中可见有永徽、元和等年号。五代以后,汉族地区此风渐衰,代之而起的是藏传佛教地区,并一直延续至今。元代始,不惟藏族地区广为流行,还随藏传佛教远传西北和北方地区。
新疆、内蒙的一些遗址都曾出土元代藏传佛教的模制泥像、泥塔。藏语将这类泥像、泥塔称为“擦擦”,《元史·释老传》载:“擦擦者,以泥作小浮屠也。……做擦擦者或十万二十万以至三十万。”足见这类泥佛、泥塔不做则已,一做则数量极多。
西藏至今没有发现相当于唐宋时期的泥像、泥塔,元代及以后的此类造像也无人作过断代分期。所以我们在分析古格遗址采集的模制泥像、泥塔时找不到可以比较的可靠资料。总的来说,这批像、塔最晚不会超过古格王国灭亡的时间,即17世纪前半叶。
但从形制、风格上看,这批像、塔明显可以分为两组。A组是从古格故城以东3公里的卡尔普遗址残塔中采集的,泥片较薄,均为浅浮雕,捺印草率,周边多不规整或有翻起的泥沿,有数量较多的塔印泥饼,造像形体简单;B组都是古格故城窑洞、殿堂中采集的,多为高浮雕,外轮廓规整,未见塔图案,造像精细,服饰繁缛,题材也显得较丰富。两组风格的差别如此之大,绝非同一时代的作品。
A组简单拙朴,具有较浓的印度、尼泊尔佛教艺术特征,年代大约可早至12世纪;B组风格已充分西藏化,与西藏其它地区的明、清时代同类作品有许多共同点,应当是古格王国晚期所制作的。两者之间没有发现过渡性的典型遗物,说明在古格王国中期模制泥像的制作可能有过一段中衰。
不寻常的面具
在Ⅳ区佛窟内堆积的箭杆中,我们清理出一件骷髅形的面具。当时,这并没有引起我们特别的注意,只是把它作为藏传佛教跳神仪式上喇嘛所戴的一般面具归档登记。晚上,我照例在烛光下记录当天的考察日志,又把这件面具拿出来仔细观察,发现了令人吃惊的内容。
面具整体呈薄壳状,外观为仿人骷髅形,后空,可扣带于人面上,用数种材料复合制成。中间是一二层涂有浆糊的本色白棉布,内外面各裱糊一至三层纸,面具外面一侧的纸上敷有一层加有细纤维的灰色薄泥皮,泥皮表面磨光并涂白色。眼窝、额窝、鼻下及上下排牙齿用淡红色涂绘晕染,两额后缘部连结布条便于系戴。面具表面泥皮已部分脱落,下颌及后侧缘也受压变形,原来的高度应有34厘米,额宽23厘米,比正常人的脸部略大,眼窝有孔,带在面部可向外观看。
这些都没有什么奇怪的,西藏其它地区寺院的跳神面具也就是这个样子。奇怪的是面具内外祷糊的纸上竟然是些西方文字,除内侧一片、外侧三片纸上是印刷体外,其余全是手写体。当时我们初识为拉丁文,但没人能看得懂其中的内容。一年之后,我们把面具带到北京,经中国天主教爱委会主教团鉴定,纸上的文字均为葡萄牙文《圣经》片断。其中面具内侧最大的一片纸上是手抄写的《圣经》第一章“创世纪”中的第39,40节部分内容,讲约瑟被卖到下埃及、受主妇诬陷被囚入狱,以及约瑟解酒政之梦等情节。
这个面具不仅是一件佛教艺术品,还是古格末期历史中反洋教事件的绝好证据。天主教传教士们千里迢迢带来的《圣经》被一页页撕开,糊成一个西藏佛教密宗的骷髅形面具,表现了古格臣民对异教的极大蔑视和征服信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