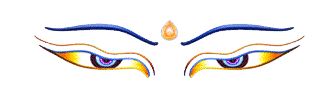法尊法师简介

法尊法师是现代著名高僧,佛学家,卓越的翻译家,不畏险阻的西行求法者,可称之为当代玄奘。法尊法师为沟通汉藏文化,弘扬藏传佛教,贡献了自己的一生。他翻译了大量西藏佛教典籍,并写有不少论著,为藏学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也是我们研究法师思想的最好材料。随着藏学研究的发展,人们会对法师的论著,深为推重,缅怀法师的功德,比肩先贤,典型百代。
法尊法师,俗姓温,法名妙贵,字法尊。笔名避嚣室主、敬之,瑜伽行者道在。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十二月十四日生于河北深县南周堡村,一九八零年十二月十四日圆寂于北京广济寺。世寿七十九岁,戒腊五十九龄。灵骨塔建在五台山广宗寺。
法尊法师自一九二一年冬于北京法源寺受戒,数十年间高风卓行,大致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三六年。法师学习西藏佛教前,先已在五台山出家,遇大勇法师,拜为师,拜为师,听讲经论,后来北京拜谒太虚法师,又在法源寺受具足戒,受戒后去南京宝华山学戒,最后又到武昌佛学院学习。从出家至武昌佛学院毕业,经过四年,法师对汉地佛学,有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武昌佛学院毕业后,回到北京参加藏文学院学习。这是法师学习藏文的开始,当时法师只有二十三岁。一年后,由大勇法师率领藏文学院全体学生出发入藏,开始了法师入藏九年的生活,先后在打箭炉、跑马山、甘孜、昌都、拉萨等地,依止大勇法师、慈愿法师、札迦大师、格陀诸古安东大师、达朴大师、格登墀巴等学习西藏各种经论。法师在《著者入藏的经过》一文中说:“在康藏留学这几年中间,要算我这一生中,最饶兴趣,最为满意的一幅图画了。”一九三三年,法师接到太虚法师几封信,催促速归办理汉藏教理院事。回汉藏教理院,仅一年有余,法师为迎请安东大师二次入藏,安东大师已经圆寂,法师悲痛已极。在拉萨依止降则法王又学习了不少经论。从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三六年共十五年,法师两次入藏,遍访名师,广学经论,随学随译,为法师成为中国历史上又一佛经翻译家,奠定了牢固的基础。这一时期的主要译著有:《菩萨戒品释》二册,《菩提道次第广论》二册,《密宗道次第论》一册,《辨了不了义善说藏论》二册,《辨了不了义论释难》二册等。
第二阶段,从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九年。法师第二次入藏归来,继续主持汉藏教理院工作,培养了大量人才。并往来于成渝之间,讲经说法。这一阶段是法师一生中作大贡献的时期,译著达到一个高潮。法师几部大的译著出自这一时期,如《地道建立》一册,《现观庄严论略释》一册,《密宗道次第广论》二册,《必刍学处》一册,《供养上师与大印合修》一册,《入中论善显密意疏》三册,译补《菩提道次第略论》一册,《菩提道次第略论止观章》一册,《修菩提心七义论》一册,以及《辨法法性论》,《七十空性论》,《精研经释》,《缘起赞释》等。著名的著作有《现代西藏》,《我去过的西藏》,《西藏民族政教史》,《藏文读本初稿》等。法师还在《海潮音》等各种杂志上发表了不少译文和论文。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法师精通西藏语文,不仅可以把藏文译成汉文,而且可以把汉文译成藏文。法师用近四年之功,终于将一部二百卷的《大毗婆沙论》译成了藏文。
第三阶段,从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六六年。解放后,法师参加了北京菩提学会翻译组,为民委翻译文件,如《论人民民主专政》、《新民主主义论》、《社会发展史》等,由汉译藏,显示了法师对西藏语文的精深造诣。五五年法师为大百科全书撰稿。五六年后,到佛学院任副院长。这一时期法师写有不少论文,在《现代佛学》上发表。然而,十分遗憾的是法师这一时期的不少译著未能出版,有些已经散佚。我们能够知道的有《五次第论》、《七宝论》、《四百论颂》、《入中论略解》、《俱舍论略解》。这一时期,法师最大功绩是翻译了一部《格西曲扎藏文字典》。
第四阶段,从一九六六年至一九八零年。"文革"期间,法师被打成黑帮,参加体力劳动,把脚砸伤致残。整整十年,法师的翻译工作是一段空白。一九七八年,法师翻译了《菩提道炬论》。法师在圆寂之前,两年半的时间里,还抱病完成了三部有关因明的译著。这三部是《释量论》、《释量论略解》、《集量论》,填补了汉文佛经因明学方面的缺典。这是法师一生中最后一个翻译高潮。
中国的翻译事业,是从翻译佛经开始的,汉文佛经基本上是从梵文翻译的。在相当于唐代的印度,佛教密宗发展到全盛时期,传入中国的西藏。西藏翻译了大量佛经,其数量远远超过汉文佛经。但有些佛经传入汉地,未传入西藏。汉地和西藏出了不少佛学家,写了不少著作。汉藏文字的翻译从唐代就开始了。吐蕃时期,有藏族大译师管•法成,在敦煌一带,翻译了一些藏文佛经,同时也把汉文佛经译成了藏文,这可能是汉藏佛经翻译的滥觞。元代有沙罗巴,已有《彰所知论》等,清代有工布查布,译有《造像度量经》等,但其数量很少。民国以来,大勇法师率领藏文学院全体学生西行求法,太虚法师创立汉藏教理院,九世班禅在北京成立北京密藏院,北京菩提学会等,翻译藏文佛经蔚然成风。有成就者,大有人在。如大勇法师,能海法师,观空法师,超一法师,严定法师,碧松法师,孙景风、汤乡铭、郭和卿、刘立千、王沂暖、古洗里•裒却多吉,虽然我们没有作细致的比较,但也可以看出,最有成就者应该是法尊法师。
法师译著颇多,有论文、论著、译著、讲记一百二十余部(篇)。根据西藏佛教的特点,法师显密兼通,几乎涉及到佛学的各个方面。如戒律、般若、中观、唯识、菩提道次第、密宗道次第、因明、历史、语言。法师翻译了不少西藏重要典籍,汉文三藏阙译本,亦有法师首翻弘通。法师第一次把藏传佛教的显密理论,系统地介绍到汉地,如《菩提道次第广论》、《密宗道次第广论》等。法师每有翻译,便融会各家,作出解释,有讲记,有释论,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法师精通西藏语文,无论是藏译汉,还是汉译藏都达到了十分纯熟的程度。历史上的翻译家玄奘,能梵汉互译。法师亦能藏汉互译。法师两次入藏,前后有十年的时间,对于西藏的地理、历史、宗教、民俗等十分了解。法师的《西藏民族政教史》是一部很有价值的历史专著,法师编译的《宗喀巴大师传》和《阿底峡尊者传》等,则记述了西藏大德祖师的事迹。法师的《现代西藏》是一本很好的教科书,对我们了解西藏大有裨益。
一九九零年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出版的《法尊法师佛学论文集》,收集了法师发表在《海潮音》、《康导月刊》、《现代佛学》、《法音》、《中国佛教》等杂志上,以及另外一些登载在其他书籍里的短小文章。法师从一九三零年随学随译开始,到一九八零年圆寂,为弘扬藏传佛教,驰骋了半个世纪,其功绩是翻译经典。而这本论文集则是法师佛学思想的结晶,是藏汉佛学研究的宝贵财产。
通过对法师文章特点的分析,从写作年代上大致分为早期文章和后期文章。
早期文章是法师第二次入藏前后写的,基本是在第一阶段末和第二阶段,有十多年的时间。这一时期的主要文章有《评藏密答问》、《答〈评藏密答问随笔〉》、《答威远佛学社驳文》、《从西藏佛教兴衰的演变说到中国佛教之建设》、《西藏佛教的建设》、《读虚大师佛教革命失败史之后》、《驳欧阳渐法相辞典叙》、《驳欧阳渐辨虚妄分别》等十几篇文章。法师游学西藏,刻苦钻研,得到藏传佛教的真传。回到内地后,看到一些人对西藏佛教的误解和不正确的认识,进行了批驳,当时法师正值年轻,理直气壮,大有压倒一切之势,同时对内地和西藏佛教如何建设,提出了一些建议,有些建议至今还很有用处。
法师后期文章,是解放后写的,基本上是在第三阶段,写文章的时间比较集中,主要是一九五三年到一九六二年这十年间。一九五五年给大百科全书撰稿,法师写了不少文章,主要是西藏的历史和几个有名的历史人物。一九五六年写了《略谈定学》。一九五七年后法师写的文章,介绍了西藏佛教典籍,如《宗喀巴大师的〈菩提道次第论〉》、《〈般若八千颂〉与〈现观庄严论〉对照科目》、《〈大般若经〉中一百零八句法简介》、《龙树菩萨的六部论》、《甘肃嘎登协主却稞寺学习五部大论的课程》。法师还写了一片关于因明的文章,题为《法称因明学中"心明"差别略说》。中观宗讲座是这一时期文章的写作高峰,也是最能体现法师佛学思想的一篇杰作。从以上可以看出法师后期文章的特点,主要是对西藏佛教的历史、人物、典籍、教理进行了论述,文章更加老练、成熟。法师的早期文章和后期文章风格迥然不同,而佛学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一九八八年台湾文殊出版社编辑印行了当代中国佛教大师文集丛书,由洪起嵩、黄启霖编,收有《法尊文集》。当代中国佛教大师文集的总序对法尊法师的评价是:沟通汉藏文化,开创中国佛教研究新眼界的一代佛学大师。在《法尊文集》的封面上,写有"汉藏文化一肩挑"的赞语。可见,海外对法尊法师的研究是十分重视的。
法尊法师入藏的经过法尊法师自述
原载《现代西藏》附录
一、 入藏目的
在民国九年的夏天,初次听到大勇法师讲《八大人觉经》的时候,我便觉着出了场子家,应当做点出家人的事情,若是一天两堂殿地混下去,实在是对不住我出家的本心!但是做什么才是出家所应作的事呢?那时候便听见老修行们说,出离生死苦海,是出家的事。什么叫做生死苦海?怎么着才能出离呢?那时候我的心理太老实了,不但不知道那两件事,就是那两个很简单的问题也不曾怀疑过。又听见一般老修行们说念佛经生极乐,是出家人的事,这些话我也直当地承认,但是在闲暇的时候,常听到勇法师讲些过去高僧的故事,我便知道出家人,不但是念佛往生和出离生死,就是在生死之中,也还有翻译经论,主持正法等,应当做的事情很多。在民国十年的春夏秋三季,又受了勇法师的指导不少。冬季便在北平法源寺道阶法师前受具,勇法师亦在冬天便往日本去学密宗,就在腊月中旬,承我的戒和尚和宝华山的八位师父的慈悲,成就我们三个北方戒子,到宝华山去学戒。在次年的夏天,听开堂师父和五师父讲《天台四教仪》,这便引发了我听讲经的宿习,我便觉听经比学戒一齐向上排班和水陆焰口的味道来得浓厚。那时偏赶上太虚大师在武昌创办佛学院,有一位戒兄,写信告诉我,说那里一天有六个钟头讲经,还有两三个钟头的自习,我见了那封信,就像小孩子要到新年的样子,欢喜得不知道怎样才好。当时就抱定了一个必去的宗旨,可是没有人介绍,又没有人做保证,怎样才能够去呢?后接到勇法师由日本的回信,他很慈悲的允许给我做介绍和保证人,我便与宝华山的师傅们作了个暂别礼,顺风向西到了武昌,拜见了太虚大师,加入佛学院的团体了。在那里第二年冬天大勇法师回到武昌传十八道,各处的佛教徒无论在家出家,都有唯密是尚的风气,我也给勇法师当过几天侍者,我也学过十八道和一尊供养,虽未受过日本带回的两部大灌顶,但觉密宗的味道,也只有那么浓厚。在已经学过教理的人去研究他,才能了解他那里头的真实道理。若是那一般全无教理根底的人去学他,只能够学到一些假像观。上焉者,得到一点三摩地影像,和本尊的加被,那就要认为是即身成佛的上上成就,谁也不敢否认他。下焉者,得到一点昏沉和掉举,夹杂着一点魔业或鬼狐神通,那也要算是即身成佛了。我的根基很弱,既没有得到三摩地影像和本尊加持,却也没有得到魔弄鬼的大神通,所以我对于密法是很淡薄的。学是要学到究竟,行是行的稳当,我既不想讨巧偷乖,又不想超次越等,更不想说大妄语自欺欺他和自害害他。我是学归学,行归行,讲说归讲说,弘扬归弘扬,样样皆以老实心自居,老实话告人,我既不想骗人,我又不想他人的利养恭敬;所以我对一般朋友们,总是毫不客气地老实话老实说,犯不着护惜他,也不怕得罪他,爱听就听,不爱听就散,有几个朋友说我对于密宗害了冷血病我也就报他冷笑一声罢了。民国十三年的春天,勇法师在北平与白普仁尊者,一同闭关于善缘庵,修护摩法,法师便觉西藏的密法,比东密来得完善,他便发了进藏求法的决心,在勇法师的初衷本想一人独往,或带一两个同志,次经白尊者及诸位大护法的劝请,才发起佛教藏文学院的组织。那个初夏也就是武昌佛学院的毕业期,勇法师在北平传十八道,函我到北平相见,面商进藏的事。盖自从入五台山亲近勇法师之后,勇法师视我,就如象他的剃度弟子一般,时时事事没有不照顾我的。他由日本归来,本想在庐山闭关修成就法,他挑中的侍者,我便是第一个。他在北平把方针一变,他对我私人的计划,当然也要变更,所以就来函找我到北平面商。我在武昌听讲《三论》、《唯识》的时候,便深慕什显奘净诸先觉的清尘,继闻勇法师入藏的函召,当然是雀跃三丈唯恐不得其门而入了。那时候,我开离父母已经六个年头了,父母劝促一返的信函,也不记得有几十封了。我那今年推明年,明年退后年的复书,当然也不会欠文字债的。这年回北平,原定的是便道回家一望,略慰父母慈怀,可是因为勇法师急于赴杭传法,便把我回家的妄念打消。到了北平,见了勇法师,商定了进藏学法的计划。勇法师南下,大刚法师、密严法师、善哲居士及我,便作了个留平筹备员,八月间勇法师到北平开学时,便带了朗禅法师、恒演法师及几位居士同来。藏文学院开学了,充先生正式上课了,我们的迦喀也渐次地上了轨道,在这开学之后,又来了超一法师、观空法师、法舫法师等。到了第二年的春末,组织了出发的团体,一路上又是传法灌顶,又是说皈受戒,热闹极了。火车便是专车,轮船也是包仓。在汉口的时候,又加入了严定法师、会中法师等。也有几位老同学,来拦住我们,说些什么母院无人,西藏难去等理由,我只笑他的愚昧固执,他并不知我早有为法牺牲的决心。西藏再难也难不过奘公所行的高昌,和显师所经的关隘。母院再无人,也有虚大师在主持、诸同学在研究。西藏既有很完善的佛法可学可译和可弘传,他们理应赞助我们,鼓励我们才对,为什么反来阻止我们呢?因为都是好同学,只有各行各的志愿,我并没有发言反对他。那年的夏天,在峨嵋避暑,顺便做了个五七息灾法会,秋天在嘉定乌尤寺阅藏及《南海寄归传》,我对于义净三藏,起了一点真实信敬心,我觉得我们中国的这些佛典经论,皆是我先觉牺牲了无量生命财产和心血身汗,更受过无量的痛苦、忧急、悲哀、热泪,才换来这些代价品。换句话说:我觉得这些经书上一字一画,便是一滴血和一滴泪的混合品,那时我们先觉发大悲心、大无畏心,立大誓愿和不顾一切的牺牲,所请来的和译出来的,我们做后学的拿起来的时候,至少也该想一想先觉的大心愿、大事业、大牺牲、大恩德,不应该自作聪明,忘恩负义地批评和诽谤。我们纵不能于先觉的辛苦事业上培福增慧,然也决不应该于先觉的功劳恩义上折福损慧才好。净法师的高僧求法诗云:“去人成百归无十,后者安知前者难。”我读那两句诗的时候,眼睛一定是个红的,因为泪珠的大小与葡萄差不多。他又说:“后贤若未谙斯旨,往往将经容易看。”他算给我们受了个预记。我受了他老人家说话的刺激,同时也受了他老人家的感化,我对于前贤实在不敢起半点轻视心,我对于先觉的事业实在不敢起半点容易心。但是先觉的这种大慈大悲和大无畏精神,我羡慕极了,我也想牺牲一切地去学学先觉,我对于西藏的佛教典籍,凡是内地所没有的,我都发愿学习翻译出来补充所缺。尤其对于义净法师所翻译的律藏,我很想给他补充圆满。西藏的密法,当然也不是例外的事。就是世间的地理、历史、工巧、医方、政治、文艺等,我也有学习的志愿。可是一个人的精力和寿量,是很有限的,能不能够达到我的目的,那就很难得预言的了。
二、 九年康藏留学
民国十四年的秋末,留学团由嘉定出发雅安了。可是这条路上是要经过好几处土匪的区域。我们全体分成了水路两道进行。自洪雅以西,就没有官兵敢做保障的。这时勇法师等,很有暂返嘉定待匪势稍息后,再继续进行的意思。但在一般处出门的同学们,是恨不能一步走到西藏的。对于土匪的危险,是毫无一点经验的,所以都很齐心的主张要走。勇法师也只好俯允我们,一方面请当地政府保护,一方面电请雅安孙总司令设法。时机很凑巧,中段的土匪也有受招安的企望,假借护送我们立一点功,所以用土匪作保商,把我们三十几个人安安稳稳地护送到了雅安。谢天谢地,才脱了龙潭虎穴的土匪窝巢。当时在雅安休息了六七天,就继续前进,由雅安到打箭炉,土匪的区域也不少,我记得由荣经出发的那一早上,遇到剿匪的军队回来,挑着几个人头是很可怕的。后来才晓得,是特为我们去除掉障碍的。第二日过大相岭的早上,又遇见土匪,可是放过了我们去,抢了后面随行的几家布商。后来才知道,也是说通了的,所以才能不抢我们。像这样走了十几天,才到了化城式的打箭炉,住在安却寺,就在这个冬季尾上,请了一位半蛮不汉的土著藏文教师,老实说一句,它的藏语虽比我们好,它的藏文实在还不如我们知道的多,过年了,开春了,同学们觉得无味了。我与朗禅法师发生了欲动的念头,不顾一切的,不问同学们愿意不愿意,我便毅然决然地要上跑马山去学经,哪怕与团体脱离关系都可以。在正式开会讨论的时候,勇法师、刚法师及诸同学都没有什么不愿意。就有一两位不愿意的,见勇法师不但不阻拦而且帮助,他也就没法反对,只有随我的自由罢了。我在跑马山依止慈愿大师住了一年,学了几种藏文文法和宗喀巴大师的《必刍戒释》、《菩萨戒释》和《菩提道次第略论》。这一年所求的学非常满意,对于藏文方面也大有进境,对于西藏的佛法,生了一种特别不共的信仰。因为见到《必刍戒释》、《菩萨戒释》的组织和理论,是在内地所见不到的事。尤其那部《菩提道次第论》的组织和建立,更是我从未梦见过的一个奇宝。我觉着发心求法的志愿,总算得到了一点小结果。哪怕我就死在西康,我也是不会生悔恨心和遗憾的了。在这一年之中,藏人的生活过惯了,专门吃糌粑不吃米面,也试验得有几分成功了,民国十六年的开春,便是我们正式出发期,我和朗禅法师是搭的甘孜拉瓦家的骡帮,装作普通僧人进藏,那个生活是很苦的。到了甘孜,就住在商人家里。勇法师是支官差用官兵护送着进藏,一路上轰轰烈烈大有不可一世之概,尤其那沿途的县长官员等,皆是争前恐后地受皈依,学密咒,郊迎郊送,川边的蛮子们,哪里见过这样尊重有礼的盛举呢?也就是勇法师的气派太大,藏人误为国家特派的大员,西藏政府来了一纸公文挡驾,并有两张通知甘孜的商人,不准带汉人进藏。障碍发生,只得暂时住下了。在四五月间,朗禅法师回到木娘乡学经。我随勇法师,移住甘孜对河的札迦寺,亲近札加大师学经去了,尔时札公年德高迈,示现残疾,名义上虽是亲近札公,实际上学经的师父,都是他老座下的上首弟子,我依止俄让巴师父,听了《菩提道次第广论》的毗钵舍那。后又依止格陀诸古,学了《因明初机入门》、《现观庄严论》和《辨了义不了义论》等多种。这位师父的年龄只比我大一岁,但是他的学问、 修行、道德和慈悲,那都是仰之弥高,钻之弥坚,不可测度的。我依止他老人家共住了四个年头,所得的利益最多。那修菩提心的教授,纯是他老人家慈悲恩予的,对于密宗深意,也由他老人家的慈悲,摸着了一点门路。我对于他的信敬心,是不可用言语来形容的事。他那慈爱的面容及那和悦的音声,令我生生世世也难得忘掉的。民国十七年的秋天,我久仰盛名的安东恩师,由廓罗来甘孜,朝礼札公,问往昌都建立道场的事宜。这是天予我的良好机会,由格陀诸古介绍,拜见了安东恩师,罄问了我积久欲问的许多难题。他老人家那种渊博学海,锋利剑芒,任你何等的困难死结,莫不迎刃而解。我受了教训之后,就五体投地地信仰,这是我初次所见的安东恩师,自此以后,就想长时依止安东恩师了。到民国十八年的八月初四日,札公大师示寂,正如人天眼灭。至初十日的早上,勇法师也逝世了,这时候刚法师在成都未回,身前只有我和恒照、密炎及密慧诸兄,这种不幸的丧事临头,我们是没有办过的,怎么办呢?慌了慌了,束手坐待是不可以的呀!于是我便东一头西一头地请格陀诸古来指导,札公的善后也是他老人家主办的,勇法义的丧事又找到他,这才见得到他老人家的真实修养,不慌不忙的,指出了一条通衢。我们几个人便依着所指示的一步一步地做下去,轻轻松松地把勇法师的荼毗事做好了。密慧兄回东古,密严兄回康定,恒照师也走了,就留我一个人在甘住守,春天刚法师和密严兄,由打箭炉来迎勇法师的灵骨回康定修塔,我也亲身送下去,重新亲近慈愿大师一个月,就在这个当儿,智三学兄也归了西。等到他的荼毗事办了,我才回到甘孜,依止格陀诸古,听受札公大师全部著述的传授。民国二十年的春天,我同朗禅法师、常光师、慧深师等四人,又进一步地到昌都去。朗禅、常光二师稍住数日即进拉萨。我与慧深师以亲近安东恩师为目的,便住在昌都求学。是年的春夏秋三季,受了四十余部的大灌顶,对于显教诸论亦略闻纲要。八月间又随恩师进藏,路过拿墟达朴大师处,依止达朴大师受绿度母身曼陀罗之不共修法等。十月底到拉萨,奉恩师之命,冬月间入别邦寺放札仓郡则,名义填在寺中,实际仍住拉萨依止恩师求学。民国二十一年,学习《因明总义论》及《菩提道次第广论》。民国二十二年,学习《现观庄严论金蔓论》、《密宗道次第广论》、《五次第广论》,三百余尊《结缘灌顶》,大威德《二种次第》及《护摩大疏》、空行佛母修法教授等。此外尚依止格登持巴听俱舍,绛则法王听戒律,颇章喀大师受胜乐金刚之大灌顶等。总之在康藏留学的这几年中间,要算我这一生中,最饶兴趣,最为满意的一幅图画了。
这几年的生活状况如何呢?我再为简略地叙述一下:当我在甘孜的第一年,是随勇法师搭伙食,吃的当然不错。第二年分开之后,我便用一个大瓦壶,满注上一壶冷水,在夜晚临睡的时候,把它安在一个牛粪充满的瓦缸子上,在给他蒙上一些御寒的破烂毡布之类,由那瓦缸内的牛粪烟子,把它渐渐熏热,乃至沸腾。到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先倒出一点洗洗脸,余者之中,放上一把粗茶半把蛮盐,这就叫做蛮茶,我在床上将早课诵毕,把它搬到床前,拿出一个木碗,半小口袋糌粑,一块酥油,几片生萝卜来用早餐。饭后便往师处候课听讲。中午回来,再喝几杯剩茶,揉上一碗糌粑吃,下午又上课去了。晚上随随便便地吃些东西,就算去了一天的时光。第二天还是原方抓药,一年三百六十天也是这一着棋。生活虽然窘迫,精神非常快乐,甚至有时候看书写书,快乐得忘了睡觉,这都是莫名其妙的事呀!在拉萨住的那几年,生活方面,差不多与前相同。学书诵经都忙得起早睡晚,连吃东西都要特别抽闲来吃。我在这八九年的光阴中间,对于西藏的显密教理,皆能略略地得到一点头绪,大概就是对于衣食住三项淡薄的缘故吧!
三、初次归来
在民国二十二年,连接的接到虚大师的几封信,催促速归办理汉藏教理院的事情,在我个人的观念上,实在觉得所学的不够用,而且想学的还很多。吃尽千辛万苦,好不容易到了西藏。放着宝所不住,哪肯轻易就回来呢?但是这里面有三种原因,我虽不愿意回来,也得回来:一、虚大师是我内地唯一无二的恩师,我对于汉文佛学,能得一知半解,皆是依止他老人家的教授得来的,他老人家是真实菩萨,终日为着整理僧伽、培植人才、复兴佛教、主持正法而忙,他在二十余年中,为扶持正法,创办学院等,不知道吃了多少苦,耐了多少劳。现在办个汉藏教理院,命我去教一点藏文,我若是违命不去,岂不是给他老人家一个绝大的打击吗?我于报恩心理上能忍耐得过去吗?二、我初到昌都时,原是想请安东恩师来主持世界佛学苑藏文系的,因为他奉DL喇嘛之命进藏,一时难得出来,我将虚大师之函件呈白,他老人家也主张叫我先出来筹备一下,他再出来,师命如是,我又哪里敢违呢?三、我请安东恩师来内地的意思,写了一道呈文,启白于DL座前,DL喇嘛的答文上,说安东恩师出来的时机尚未到,顶好是我先出来。这个答复,更造成了我先归的铁案。就在那年十月二十七日作了我初次归来的行期。在行期的前六天,便是我好友朗禅法师圆寂忌日,他是害热病死的,在九月间他害了两次,幸喜DL太医的手段高明,皆给救住。第三次病返在寺中,离拉萨太远,没法延医救治,所以他就呜呼哀哉了!我对于他的期望心很重,我回内地筹备之时,还望他能时时代我劝驾恩师的,谁知他这一死,便弄得我后方接应无人,所以我对于朗法师之死,伤心极了,就在伤心之中,也勉强代他办理了丧事才动身,我那时觉得人生太无常了,太萎脆了,稍微遇着一点违缘,便要分出此世与后世的界限。西藏这块净土,今天一别,实不知还能不能重来!所经过的印度,即是我释迦牟尼如来诞生成佛说法示寂之国土,这些圣地若不饱饱的朝礼个够,下次能不能再来圣地,那更是不可预料的事了。因为这个无常观念,时时逼在我眼前,我便会狂了似的,由戈伦堡,直往金刚场,住了七天,修了点供养。又往鹿野苑朝礼转法-轮塔,又往拘尸那双林佛涅磐处朝礼一遍。次往尼泊尔,朝礼佛往昔施身喂虎等圣迹。这样转了一个多月,直到民国二十三年正月里才到加尔加大,又往国际大学看望一位故友,住了三天,回来便买舟东渡,往仰光朝礼大金塔去了。那里有慈航法师首创的仰光中国佛学会,会上同仁,对于做弘法利生的事业很有精神。我在福山寺里挂单闭关,住到三月底出关之后,在佛学会随喜了几次普通演讲。到四月初四那天,我便买轮归国,五月初到上海,特往奉化朝谒虚大师。在雪窦寺住了七天,便回上海往南京,会晤了谢次长、周局长、邓梦先、陈济博等一班故友,承密师父的涵召,重游宝华山。开堂师父已做了和尚,密承师也接了法卷。后往北平避暑,给安钦大师任了一夏天义务翻译。回家省亲一次,这是我离家以后第二次回家了。先是十四年四月里临赴藏的时候,回去过一次,那时我的双亲还在,唯慈母大人,因为我出家永别的关系,昼夜恒哭,哭得右目失了明,我觉得父母对于儿女的心太切了,恩太重了。但若叫我守在牢狱似的家里事亲,那是绝对做不到的事,假若出了家不务如来的正业浪费时光,非但对不住佛及师长,就连我的慈母也没法见面,这也是我学法志坚的一段小因缘。二次回家的时候,我的慈父已经去世了五年,后期的侄辈大多数没有会过。连探亲里一共住了十天,七月底到的武昌,八月间赶到汉藏教理院开学。代理虚大师的那副千钧重担,轻轻地就负在我的肩上,每天讲三小时的课,还要翻译校改《菩提道次第广论》、《密宗道次第略论》和《菩萨戒品释论》等的文字。这里埋头苦干了两学期,二次进藏的机会就成熟了。
四、再度入藏
我这次归来的计划,是想筹备一下迎安东恩师的,如上段已略略地说过。我想迎师的原因,便是我觉得一个人用尽一生的精神去求学,也难得学好和学完善。尤其想翻译经论的同志们,对于汉文和佛学必须先有相当的根底,学好藏文佛学之后,才能够正式翻译。不然,就是将藏文佛学,学到第一等第一名格什的程度,仍然是个藏文佛学的格什,遇见真正翻译的时候,仍不免默然向隅。那与翻译经论和世间书籍,何益之有也?我若用尽一生精神,去专学藏文佛学,也不愁做不到第一等的格什,可是时间上许可我吗?虚大师允许我吗?恩师上人准许我吗?不,不,他们都不许我那么做。尤其是退位的老格登持巴大师,曾经教授我说:“你在三大寺,就熬到第一名格什,渐次升到格登持巴,想我这样头上打着一把黄伞,这也是干枯假名,对于佛法并无多大的益处,你如今先回去把宗喀巴大师的《菩提道次第论》翻译出来,在你们汉地建立起座正法幢来,那才对于佛法和众生做了真实的饶益。你若能设法将绛热仁波卿(安东恩师之名)迎接出去,把宗喀巴大师的显密教法,建立起来,那比考格什升格登持巴的功德,大得多哩。”他老人家的这几句话,固然是安慰我学业未成中途而返痛苦的方便谈,但是也给了我虚荣心的一个大顶门针。由此便造成了我第二次的进藏。我是志在翻译的,我的学业是未造成功的,若无一位显密圆通学德兼优的大善知识随时指导,我想翻译的事业是不会圆满的。我第二次进藏的目的,就是想迎我那位名满康藏位居王师的安东恩师出来弘法的了。
民国二十四年夏天,承阿旺堪布及蓉方学佛同人的函召,到成都去讲了一次经。蒙诸大施主的捐助,凑够了迎师来内地的路费。八月底回院,将院务全权拜托教务主任苇舫法师代理,于古历九月初一日,便下山东渡,绕道山西朝礼五台及大同云岗。道经平津,唔诸旧友,请其捐助印行《菩提道次第广论》。此论印行成功,全赖平津诸友乐施的功德。十四日观光菩提学会成立典礼,留下了永不可忘的一点印象。十九日买轮南下,二十四日抵香港,住佛学会。二十八日又买轮南行,古历冬月初三日抵新加坡。船再北行,初十到仰光,住曾文银老居士之花园中,休息半月,应酬了些世法。二十六日买轮赴印度,二十九日便到加尔加大,住唐人街天益楼平商德茂永宝号。这晚阿旺堪布等亦到印度。因为携带的丝织品太多,海关上给扣留要税,这次见到行李太多的麻烦了。我也帮着到处托人设法。后由西藏政府来了个电报证明,英国人立即放行免税。英人对西藏的怀柔,真是令人不寒而栗。古历腊月十一日赴戈伦堡,预备进藏所需的一切行装。十八日与叶增隆先生一同雇骡帮进藏。为避英人的阻碍起见,凡至关隘,必须隐居密室,半夜步行逃过。一因年余来少于步行,二因新做的皮靴太紧,在十九日的下午便将两足后跟磨坏了两块,挤落了三个指甲,痛得我万分难忍,一步一咬牙,晚上住在桑零曲喀,一步也走不动了。在这一生之中,我算第一次受这种罪,我知道为法牺牲的诸先觉,也是吃过这种痛苦的,我在往昔生中,被贪嗔痴等所使,为追逐五欲所吃的痛苦,必大于这种痛苦的百倍。我今生出了家,为迎师弘法起见,吃这一点小苦,实在是应当值得吃,在这三界之中,吃这种痛苦和更大痛苦的众生多得很,他们实在是可怜,我应在此痛苦之上,代尽一切有情受尽一切痛苦,唯愿没有一个有情再受痛苦。我这样地推想了一阵,于是把脚上和身上的痛苦忘掉,瞌睡来了,我就朦胧睡到天亮,次日又勉强能走几步了,这样一天一天的连痛带病的熬到二十四日才到了帕克里,住在恒盛公大宝号,承马义才先生的优待,修养了几天,二十八日雇了白字仓两匹骡子,我与增隆一同赴藏,古历正月初一日,在途中最高寒的卡炉过年,除夕增隆煮了一些稀饭给我吃,--我病已久,一路全仗增隆照顾,同乡之情,深觉可感,--还说了两句笑话,便是说:“以后过快乐年的时候,别忘了我们的今天呀!”这样熬了十天,民国二十五年古历正月初九上午到了拉萨。在藏的同乡们皆出郊来接,同乡们在异域相遇,比亲兄弟还觉着亲热。出十见到安东恩师的管家,交来恩师手谕两件,是说他老人家绕道动锡,不来拉萨,叫我在拉萨请所需的书籍数驮,直回帕克理会齐东来。拜读之后,欢喜得嘴都合不起来,精神为之一振,身上的病痛也就消失了一半。在十四日的早上,忽见管家匆匆而来面带惊慌之色,我急问何事,他便说拿墟来了专差,恩师上人于初二圆寂了。哎哟!天呀!呜呼!苦哉!好象有一口热血,直往上涌,幸喜裁止得快,未曾昏倒。稍为叹息了一会,便急匆匆地往各处佛殿供灯,并发一长电告之内地诸檀越,十六日随管家等往拿墟。在止公地界遇天降大雪尺余,以后沿途尽是冰天雪地,更加是露地食宿,遂犯了腿部转筋的旧症,并新添了痢疾。三十日始到绒波寺,这是恩师圆寂的处所。在寺修养了几天,才加入代恩师修法的团体。古历二月十三日,为恩师荼毗日期,众人一致推我主法,乃以大威德护摩法焚化。十九日收检骨灰,于中捡得舍利子数粒。四十九日法会圆满后,又修护法神供养法数日,于古历二月初三日,结伴三人,先返拉萨。途中复遇大雪,露地生活较前次更多。因来时支有官马,沿途牧场尚可借宿,归程全系自马,唯可放牧野原觅柴自炊耳。直至十八日晚上,才到拉萨,住在同乡处。人困马乏至此为极。此后在拉萨养病,凡阅五月,即在此期中,亦依止绛则法王,听讲《菩提道次第略论》、《必刍戒广释》和《俱舍论》等。自于每日略译《辨了不了义论》一页半页不定,总以不空过为限耳。第二次进藏的情形大概如此。
五、重归和志愿
迎师是扑了空,在夏季之中,虽亦另访了几位。有的是不愿来内地,有的是为事所阻,结果没有一位能同来。在八月连奉虚大师及汉藏院电信,促我速归。遂将所请之经书,包扎成驮。唯因时期尚早,河水未退,无有商人往返印帕间,我因回国心急,解友三先生,特派骡帮送印,只因经书太多,延时过久,古历十月初五,始到戈伦堡,住惠文皮工厂。将经书交转运公司转运。初十日即赴加尔加大,住与记宝号。十一日签回头护照,十八日买轮东归,惟在我动身之前,经书尚未运到,实属憾事!只好拜托友人到时再为转运了。冬月初五日抵香港,是晚即乘车赴广州,转粤汉车,初八晚两点半至武昌,住佛学院。在武昌住了半个月,讲了一部《二十唯识论》和《菩提道次第修法》并《菩提道次第广论》中奢摩他的前半段。二十五日偕法舫法师、雪松法师、契惺法师乘武林船西行。二十九日到宜昌,三十日买民安轮票。古历十二月初一日开驶,初三日船在兴隆滩触礁,几乎葬身鱼腹,枯水行船,实在是令人胆裂。水手门七忙八乱地涂了些洋灰,勉强走到盘沱住宿。初四开到万县,赶忙换民苏。初七晚才到重庆,初十始平安回到缙云山。
回院后,很想休息调养几日。不过我是为佛法而发愿牺牲的,院务忙得很,并且离院一年多,全权是请苇舫法师代理的,把他辛苦了。专修班的课程,多蒙严定兄担任教授,我更是感谢到了万分。其余的各位教职员,都各负其责地热心做事,没有一位不令我感激的。我自己空跑了一趟,耽误了一年多的光阴,实在惭愧如地。迎师既未成功,事情乃当自做,肩头要硬些,脚板要直些,每日除在普通专修两科中教课外,尚需为法师们讲点戒律和密法。再有空闲,便是做我私人所愿做的翻译工作了。只要能够与佛法有真实利益,译书、教课、栽培后学,这当然都是我分内的事了。
法尊法师自述
法尊俗姓温,河北深县人,一九○二年生。在俗时仅读小学三年,文化很低。一九一九年,因家境困难,到保定府学做皮鞋。因长期患病,学业无成,与一九二○年春末,厌世逃往五台山出家,投玉皇庙瑞普(法名觉祥)师座前落发,法名妙贵,字法尊,即在庙随众劳动。早晚学习念诵功课。
是年秋,大勇法师、玄义法师等路过本寺,遂请勇师讲开示,勇师即日略讲《八大人觉经》,次又讲《佛遗教经》,遂对听经发生兴趣。
一九二一年春节,广济茅蓬打念佛七,我去参加,七后即住在茅蓬参学。是夏听大勇法师讲《弥陀经》等,又听远参法师讲《梵网经》,对经论中的名相有了点粗浅的理解。
是年秋,太虚法师应北京佛教界邀请,在广济寺讲《法华经》,大勇法师要到北京听经。是年冬,法源寺道阶法师将传戒,我要到京受戒,遂跟随大勇法师到北京,礼谒了太虚法师,听说准备办武昌佛学院,予请入佛学院学习,蒙太虚法师面许。是冬在法源寺受戒后,即随传戒诸师到南京宝华山隆昌律寺学习传戒法。
一九二二年夏,在宝华听讲《天台四教仪》,兼阅《教观纲宗》等,对天台教义,略有所知。冬初,听说武昌佛学院开学,遂下宝华山前往武昌。在佛学院先学《俱舍颂》、《因明》、《佛教史》等一般论述。次年则听讲"三论"、《解深密经》、《文殊般若》及《成唯识论》等大乘空有两宗的要典,又听了《密宗纲要》等。对于大小显密得到了一个轮廓认识。
一九二三年冬,大勇法师由日本回国,在佛学院传授十八道,余亦预其法会,学了文殊修法。
一九二四年,大勇法师在北京筹办藏文学院,准备学习西藏所传的教法。是夏武昌佛学院毕业后,我即回北京参加藏文学院,进学藏文。
一九二五年,太虚法师在北京中山公园讲《仁王护国般若经》,又在藏文学院讲《摄大乘论》,余均预法会。是年初夏,藏文学院全体出发进藏,路经武汉、宜昌、重庆,后到嘉定,登峨眉山避暑、打七。秋初下山,因无走山路经验,下山急跑,将到山脚时,两脚已寸步难行。抵达万行庄时,已日没很久,次早起床,足不能履地,在庄上休息数日,始返嘉定乌尤寺。
在万行庄休息时,见室堆有大藏经,遂翻阅律藏数卷,到乌尤寺后,遂借阅《根本说一切有部律藏》。同时为加紧学习藏文,手抄《四体合璧》一书中之藏汉名词(世俗语)四册,又抄日本出版的《四体合璧翻译名义集》中汉藏文名词(佛教语)四册,作为随时参考的资料。
是年冬,经雅安,越大相岭到康定,住安却寺,特请一位邱先生教藏文,前在北京藏文学院教藏文的充宝林先生,即康定充家锅庄人,是康定跑马山慈愿大师的弟子。旧历年底,充先生亦回康定。
一九二六年春,大勇法师,朗禅法师和我同上跑马山,亲近慈愿大师,先学藏文文法《三十颂》、《转相论》、《异名论》、《一名多义论》、《字书》等关于藏文的初级书籍。次学宗喀巴大师讲的《必刍学处》、《菩萨戒品释》、《菩提道次第略论》等佛教正式典籍,为学习藏文佛学打下了一个较好的基础。
一九二七年,大勇法师率领一部分同学支官差进藏,我和朗禅法师则搭商人拉噶仓骡帮进藏,抵达甘孜时,西藏政府来信阻止汉僧进藏(当时康藏有隔碍,疑心我们是政府派遣的,所以阻止)。我们因此就住在甘孜札噶寺学经了。
我在札噶寺依札噶诸古数年,初学《因明入门》等书,次学《现观庄严论》(参阅各家注疏)、《辩了义不了义论》,听受了札噶大师的著述和许多传记文类。我在这期间内,试译了宗喀巴大师的《缘起赞》并略加解释。摘译了《宗喀巴大师传》和《阿底峡尊者传》,俱在《海潮音》上发表。还译了几种小品教授,今已遗失。
一九三○年(记不准了)春,到昌都亲近东格什,适值传金刚蔓论法会,受该论中四十多种法。夏季学了一点声明知识(可惜未学全),秋后随安东格什进藏,冬季抵达拉萨。
一九三一年以后,依止安东格什,学了《菩提道次第广论》、《密宗道次第广论》、《密宗道建立》、《五次第论》、《入中论》等。又在此时,开始译《菩提道次第广论》,是时汉藏教理院已成立,太虚法师多次来信催促我回来教学,遂结束学业。
一九三三年冬初,离开拉萨,搭商帮,往印度,准备由海道回国。在印度期间朝礼菩提扬、波罗奈斯、拘尸那等圣迹后,又往尼泊尔朝礼许多圣迹。
一九三四年春,到缅甸仰光,朝礼大金塔,住到初夏,乃乘轮经槟榔屿、新加坡、香港,六月间抵上海,到宁波育王、雪窦,谒见太虚法师,汇报数年来学法的经过。次回上海,到南京小住,安钦大师为南京诸信士传吉祥天女法,邀余代译语。次到北京,回俗家一望。是夏安钦大师为北京佛教界在密藏院传法,余为译语。仲秋乃经武汉,入川到重庆汉藏教理院,担任了教学工作兼管理院务。是时继续翻译《菩提道次第广论》,为同学讲授。又举《必刍学处》、《菩萨戒品释》等。
我原想迎请安东格什来内地宏法,以便学习一切未学到的教理。但迎请大德必须有足够的经费,而筹此费用,亦非易事。是年年底会见了阿旺堪布,彼邀我到成都讲经,以便筹款。时有胡有章居士到汉藏教理院,亦极力劝我去成都讲经,为迎师筹款为宜也。
一九三五年夏,应阿旺堪布之邀,遂赴成都,先为阿旺堪布译语,讲颇章喀大师所造之《发愿文》。次讲宗喀巴大师的《缘起赞论》。筹集了迎请安东格什的路费。秋季,即再度进藏。冬季到拉萨,但因缘不具,不久安东格什圆寂,我数年计划全成泡影。世法如是,无可奈何。
一九三六年,依止绛则法王学法,听讲《必刍戒》(德光论师的律经)、《俱舍论•随眠品》等,是年在拉萨翻译《辩了义不了义论》及《释》,《菩提道次第广论》及《密宗道略论》,在武昌出版。秋后仍绕印度由海路回国,请回《藏文大藏经》和宗喀巴师徒的著作等。
一九三七年夏,到武汉,准备到北京参加安钦大师传法的法会。因"七七事变"未果。秋后请太虚法师一同入川,在汉藏教理院讲学。是时承太虚法师嘱,遂翻《密宗道次第广论》,后由北京菩提学会印行。
在抗日战争期间,除在汉院讲学外,还编写了《藏文文法》、《藏文读本》,翻译了《入中论善显密意疏》等。又受东本格什嘱托,将《大毗婆沙论》二百卷译成藏文。又为讲授西藏的佛教历史,编写了一部《西藏民族政教史》。也曾代国民政府教育部编写《藏文课本》八册,《常识课本》六册,并未出版。一九四八年暑假后,余将汉藏教理院事付托正果法师和开一法师等负责办理,遂到成都讲经,并加紧翻译《大毗婆沙论》。一九四九年夏译完,将译稿运往康定交格桑悦协保管,完成这件大事,不负东本格什之所托也。
一九四九年冬,四川解放后,我非常想家,因为多年来战火连绵,尤其我的家乡是日寇扫荡区,不知家中尚有人否,所以归心很切,急想回去看看。在旧历腊月初离开成都,经重庆、汉口、石家庄,一路很顺利,腊月底到家,幸老母尚健在,全家也粗安,不胜喜慰。在家住了月余,并探望了各处亲友。
一九五○年春,我来北京菩提学会参加了翻译组,替民委翻译文件。是冬,正果法师来京和我商议把汉藏教理院奉交西南文教处事,我完全赞同。遂将汉院交给政府,汉院的师生也由政府安排工作。汉藏教理院也就结束了。直到一九五四年间,翻译了《论人民民主专政》、《新民主主义论》、《社会发展史》等,又将却扎编的《藏文辞典》译成汉文。又译出《五次第论》和宁玛派的《七宝论》。
一九五五年,为佛教百科全书撰稿十余篇。辞去了民族出版社的工作。
一九五六年秋,中国佛学院成立后,任佛学院副院长,兼讲授佛学课程,译了《四百论颂》、《入中论略解》、《俱舍颂略解》等。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中,佛学院解散后,我被打成黑帮,参加体力劳动。一九七二年,解除黑帮名义,恢复自由。一九七三年后,患心脏病,养病至尽。
法尊作于一九七九年八月六日 |